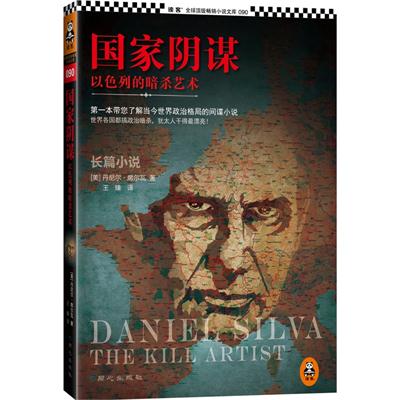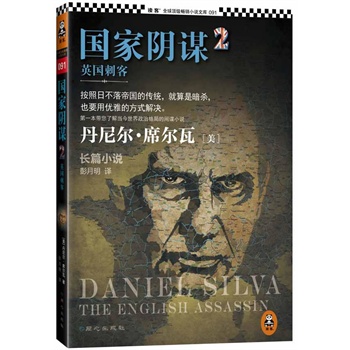国家荣誉-第7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天牧没想到钟成的妻子如此朴素: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普通的短发中夹杂着不少的白发,脸盘挺秀气,身材削瘦。她平和地说:“我早上接到办公室同事的电话,说有个记者要采访我。我说,别来了,有啥采访的,她们没给你说我的态度吗?”
马天牧笑笑,执著地说:“她们说了不让我打扰你,说你刚做了手术,可我打定主意要采访你,反正你在家也挺寂寞的,我呀,就坐在床边跟你聊聊天好吗?”
钟成的妻子李玉梅无奈地笑笑:“那就坐吧,我给你倒杯茶。”
马天牧连忙把李玉梅拽到床边:“大姐,别动,你要是喝水,我给您倒去;如果不喝,我也不喝,我是属骆驼的,耐渴。”
李玉梅的身体还很虚弱,她说:“那我就躺下了?”
“这样最自然了,我心里的内疚也少了点。”马天牧到洗手间冼了个手,然后,坐在床边给李玉梅削她带来的水果。
马天牧随便问着:“大姐,你跟钟局长结婚几年了?”
李玉梅抿着嘴笑:“呀,一眨眼,两人在一起也混了十五年啦。”
“你们是自己认识的还是别人介绍的?”马天牧开始刨根问底了。
“嗨,怎么说呢?一切都是缘分。那年我十九岁,当时理想是当画家,我从小就学画画,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雄心勃勃地报考了中央美院,专业课分考的挺高,但政治和英语丢分太多,高考落榜了。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鼓励我再复习一年,我也有这个信心。但谁知,几天之后,我自己又变了。那天,我神使鬼差地溜达到公安局附近,当时,公安局门口围了许多青年人,我凑过去一看,原来公安局正在招收警察。我从未想过当警察的事,可那天,我一下子被女考官那身好看的警服吸引了,多美啊,多神气啊,于是,我自作主张地报了名,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警察。入警一个月后,公安局团委搞新老警察联欢,上高中时,我的舞就跳得特棒,而且不怯场。那天,挺高兴地代表新警察们跳了个新疆舞,这一下,被钟成看上了,准确地说,是被钟成大学时的同学看好,他极力推荐给钟成说,‘看这姑娘多水灵啊,像葡萄一样,不抓紧下手,一个月后,追她的小伙子得排长队。’钟成特别在意这个同学的看法,于是他就憨乎乎地约我出来,我出来了,他又什么也不会说,我就想,咋还有这么老实的大学生呢?我把钟成的情况如实向父亲汇报,因为我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我从不说谎,母亲问我钟成家的经济状况好吗?我说,他家四个孩子,他是老大,经济上很困难。母亲问我喜欢他吗?我说有点喜欢。母亲又问喜欢他什么?我说他老实。母亲说他的经济条件不好,以后你要吃苦,你会不会后悔?我说不会。母亲说,那你自己定吧。一年之后,我们结婚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跳过舞,我的舞台变成了锅台。”
马天牧突然侧脸问:“大姐,你觉得跟他过幸福吗?”
“这叫我怎么说呢?酸甜苦减辣的感受都有。我的同学当中,好多夫妻都过着过着就散了,但我们俩不会散。有时我就想,这幸福啊,要看是怎样一个标准?如果从一个女人需要丈夫关心,需要丈夫呵护这点来说,我不幸福。在这点上,钟成做得不好,非常不好,但我也知道,他不是对我不好,而是没有时间对我好。如果从一个女人为自己的丈夫而骄傲来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丈夫是个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而且工作的很出色,得到大家的敬重。他出差在外,我只为他工作是否有危险、高血压病是不是又犯了而揪心,从来不考虑他的人品有问题。他对家庭、对我们的感情绝对忠诚,就这点而言呢,我又觉得值了,我找了个好丈夫,真的,十五年来我不仅爱他还敬重他。”李玉梅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说这些话时,她的脸上竟泛着红晕,而且说到激动处,目光有些潮湿了。
马天牧伸出手去,轻轻拉了拉李玉梅的手说:“大姐,你说的真好,平实中见真情。”
李玉梅说:“十年前我还不能这样冷静地想问题,那时年轻啊,受了委屈就想跟他闹,可他从不跟我计较,甚至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你知道吗?他才叫大聪明呢,表面上是我吵吵嚷嚷的,好像他脾气好得不行,其实,吃亏的是我,人家嘻嘻哈哈的照样一件家务活都不干,我就跟个傻牛似地,整整干了十五年,把自己累成腰椎间盘凸出,把自己累得胆襄切除了。”
“钟局长知道你做手术吗?”马天牧关切地问。
“我哪儿会告诉他?就是跟他说了,他也没时间回来照顾我,他心里还急;而我也抱着希望等他来,如果希望达不到,我会更失望。所以,没必要,还不如我自己解决,自己照顾自己。这些年啊,习惯了。怎么样?我发明的这种心理平衡法,把自己医治的还挺健康的吧?”李玉梅爽朗地介绍着她的感受。
马天牧竟然忘了记录,她像一块干燥的海绵,贪娈地吸收着李大姐用经验累积的水份。她的经验之于马天牧太珍贵了。
马天牧比较着说:“那这么说,你和钟局长之间其实是不平等的,你对家庭的付出远远超过他。”
“何止不平等,是绝对不公平。女儿是我一手辛辛苦苦带大的,但女儿却跟他感情好得不得了,你说这公平吗?平时家时里买米买面的活都是我干,还有搬家,全是我一个人洗涮,一个人打包,一个人找那种板车,又拉又扛的,钟成只是在有时间的时候回来看看,他最多对我说谢谢,感动极了也会抱我一下,嗨,我这人就是贱,人家就那么表示一下,我跟个牛似地什么都大包大揽了。现在有人一提搬家,我头皮都麻,跟他结婚十五年,我们光搬家就有十几次了,没办法,他的工作需要呀。有一次我们单位拉煤,整整一吨啊,我硬是一桶一桶自己拉回家的。那天,我母亲正好来看我,她心疼地说,‘你明天肯定起不了床’,但第二天,我咬着牙起了床,钟成不在家,女儿要上学,我还要工作啊。我这人看上去瘦弱,其实非常坚强,在工作上,我从来不沾钟成的光,而且要求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好。地区公安局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是钟成的老婆,我对外人也从来不提钟成,为什么?他已经够忙的了,我不想给他添麻烦,我为他着想的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理解他的工作,但从不过问他的工作。还有一次是冬天,我自己倒腾一个几十斤斤重的铁炉子,那次,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腰部“嘎”地响了一下,当时我就不能动了,腰椎间盘凸出了。接着,我哇哇吐起来,吐完又哇哇大哭,我哭我自己的腰断了,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女儿放学回来,一看到妈妈这个惨相,吓得跑到单位去找爸爸,钟成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要开刀,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下半辈子完蛋了,得在床上过了。那时我恨死了钟成,想,一旦我能站起来,我就跟他离婚,不过了。”
马天牧吃惊地打量着李玉梅说:“大姐,没想到你还有过这样的苦难史,那么后来出院之后,你跟他提离婚的事了吗?”
“嗨,那都是气头上的想法,我怎么舍得离开他呢?”李玉梅不好意思地说。
马天牧问:“从那以后,钟局长是否有内疚感呢?”
“他对我其实一直都很内疚。我不是说了吗,他想对我好,但在工作和我之间他无法兼顾,如果他是个普通警察,可能还有点时间,可他是个一局之长,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要管,自己还有高血压、心脏病什么的,我不可能让他为了这个家,局长不干了吧?就算他不当局长了,可我不能让他连警察都不干了吧?我自己就是警察,起码的政治觉悟还是有的。这个社会上总要有人当警察吧?这么一想,什么事都通了。我就对他说,钟成,你也就是找了我这样的好身体,如果找个病秧子,看你怎么办?钟成认真地想了一下说,那还真难办了。”
“这些年,你除了觉得吃苦受累挺委屈,还有别的委屈吗?”马天牧暗示性地提问。
“有啊,刚进门我就跟你说了,我爱画画,想当画家是我一生的梦想。可是要当画家,就得花钱,花时间,还参加一些沙龙活动什么的。钟成就跟我商量说,‘你看咱家本来经济就困难,还要支援母亲那边。再说,搞艺术的那些人思想比较开放比较乱,经常约你出去也不合适吧?我老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谁照看孩子,谁照看家庭呢?这样吧,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我给你布置个画室,让你画个够’。钟成这家伙哪是在跟我商量,而是在强硬地要求我无条件服从,我也只好服从,如果我反抗的话,两人的感情矛盾肯定会激化,怎么办,我只有做出让步。这一让就是十五年过去了。这不,这次女儿读初中坚决要求去住校,我女儿的个性特别强,主意也大,这点像她爸爸,她还说初中念完之后,自己要到乌乌鲁木齐去读高中,将来到北京去读大学,然后再到国外去读研究生,心野着呢。女儿住校了,钟成说要给我腾出个地方做画室,让我把年轻时想干的事都干了。我倒也这么想啊,可是感觉不对了,拿起画笔不知画什么,而且身体也不行了,腰痛的直接就坐不住,我也曾参加过一次艺术沙龙,可能是老了,也可能是没作品,那些年轻人都不跟我交流,我在那儿呆了一会儿,就回家了。钟成问,怎么回来了?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想画的时候就在家里画画吧。钟成检讨自己说,‘要不是嫁给我,你也许是个著名的画家了,你后悔吗’,我说,现在就别说后悔的话了,我现在不是有个挺美满的家吗?人活一生,哪能都事事如意呢?跟那些散了的家庭相比,我不知幸福多少呢。”李玉梅一口气讲了那么多她和钟成的事情,发了那么多感慨,对马天牧的触动很大。
马天牧道:“大姐,我从你对钟局长的‘控诉’中,倒听出一种深深的爱情,我确信你因为爱他,才心甘情愿地当贤妻良母的。”
李玉梅笑着说:“谁说不是呢?”
“你觉得值了?”马天牧道。
“值了。”李玉梅肯定地说。
马天牧从李玉梅家出来时,落日已经与地平线上溶为一体。李玉梅坚持把马天牧送出门去。她站在款款的落日里,尤如一尊亲切的母亲的雕像,久久地目送着亲人远去或盼着亲人归来。
马天牧几回首,心中都涌动着一股热流,她发自内心地感叹:多么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人。
第十五篇第二十九章(2)
二
马天牧从钟成家采访回来,很激动,她情不自禁地又拨了一次王路的手机,幸运的是,竟然通了。她忙问:“王路,你在哪儿?我想过去看看你。”
王路和亚力坤正在审枪贩子卡拉,他一听是马天牧打来的电话,就站起身跑到外面去接电话。王路来到楼梯的一侧,他问:“你还在南疆吗?怎么还没走?对不起,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这儿正忙着呢,得把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