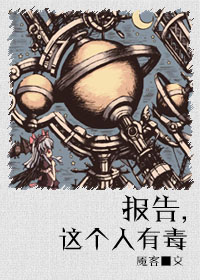鸳鸯茶 作者:妮娜-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我被他的话触动了,“你被人善待,你以后也一定会是个好父亲。”
他的目光停顿在我的脸上。我坚信不移地朝他点点头。
我给他讲了一个在我童年记忆里故事:“小时候我们住在江南的小县城,长到十二岁我们才回北京。我的父母是医生,我们住在县医院的家属宿舍,我们的隔壁邻居住着医院的电工,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名字叫扬扬,他和我同年但他的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他的脸黄黄的,头发也黄黄的,又稀又细,在天气干燥冬天,他的头发就竖起起来,用手一碰就会‘啪、啪’发出火花。他有个哥哥,看上去比扬扬长得漂亮,皮肤白里透红,头发又黑又密,但是他却是个天生的弱智,双目失明,虽然那时已经九岁了,却仍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有一天,我正在和扬扬玩,他的傻哥哥躺在床上突然翻起白眼,口吐白沫,喉咙里发出怪声。扬扬赶紧跑到门外叫来他的妈妈。扬扬的妈妈正在门外面晾衣服,她赶紧跑进屋,麻利地往傻子咬得紧紧的牙关间塞一块湿毛巾,防止他咬伤舌头。她看着怀里抽搐的孩子,眼泪无声地掉下来。后来,我看见扬扬的妈妈坐在傻孩子的床边,一边抚摸着他的头发,一边用奇怪的像小孩一样的声音那样说话;‘多可惜呀,你看你呀,你长的多端正呀,这么白的皮肤哟,这么黑的头发。’ 那傻孩子朝着他的妈妈,他的斜视无光的大眼睛睁大,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带着古怪的笑,‘咿咿呀呀’地回应着,用后脚根把床板敲得铛铛响。母亲看着孩子,她的目光里充满了爱,这是全天底下最伟大的母爱。
我吃惊地看见一滴眼泪从查尔斯的眼角淌下来。他用大拇指抹去眼泪,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
大概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而我们毫不相关的儿时经历一下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喝完茶,查尔斯建议我们出去走一走。在大堂的一隅,开设了一个中国手工艺品的专柜,里面精致的工艺品玲琅满目:有北京的锦泰兰,宜兴的紫砂壶,景德镇的磁器,苏州的双面绣等等。在一幅木雕的屏风前,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妙龄少女坐在一张仿明式的书案后,聚精会神地在一只鸭蛋大小的鼻烟瓶里画内画。她左手轻轻地托着小瓶,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只细细的特制的毛笔,她将笔杆伸进窄窄的瓶口,随着手指的微微地移动,她在鼻烟瓶内描绘出一幅古代仕女图。查尔斯对她精湛的技艺连声感叹:“这怎么可能? 真不可思议!”在穿着红旗袍的妙龄少女书案前,一个铺着黄色锦缎的盒子里陈列着已经画好的鼻烟瓶,有金陵十二钗仕女图和一些花鸟画。查尔斯买了一个绘着花鸟的鼻烟瓶送给我。我也买了一个绘着仕女图的小瓶子送给了他,并囫囵地向他介绍了《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他似懂非懂地听完了我的介绍,索性买下了一整套。我没想到我的故事会达到这样的效果,画内画的女孩也高兴得喜笑颜开。
第三章 鸳鸯茶(3)
我们和画内画的女孩聊了一会,查尔斯问了她几个问题,我帮他翻译。她给我们讲解一些技巧,又做了几个示范。我们又在一旁看了一会儿。
我觉得时间不早了,我向查尔斯告辞。
临分手的时候,查尔斯问我,星期三可不可以再见到我。
我抿嘴笑着朝他点点头。
第三天的傍晚, 教研组的其他老师下班都回家了,我独自留下来备课,准备学生期末考试前的总复习。我一边写教案,一边不时地看看手表。七点半,我按查尔斯约定的时间走出校门,在校门口的路灯下,一辆黑色的林肯牌轿车车头灯闪了一下,向我发出“信号”。我停下脚步,查尔斯下了车,走到乘客位旁,颇有风度地为我打开车门,这些殷勤的细节赢得我的好感。他发动了引擎,说要带我到了前门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涮羊肉。
我们一推开餐馆的门,一阵香味扑鼻而来,饭馆的老板看到查尔斯先一愣,明显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他的反应很快,脸上立刻堆满殷勤的笑容:“啊,来来来,请进请进!来了位外宾。您是他的翻译?”我含含糊糊是事而非地“嗯”了一声,我不想跟他多解释。我心里奇怪查尔斯怎么会找到这么地道涮羊肉馆。馆子店面不大,靠墙放着几张饭桌和板凳,空气里飘散着涮羊肉和清真佐料的香味,油烟和热气把四周的墙壁熏得发黄,饭桌和板凳都布满了油渍的。我们坐下后,查尔斯告诉我,他在来中国前看了一本美国出版的自助旅游书上提到这家馆子,据说是北京的原滋原味的涮羊肉餐厅。一会儿,冒着热气的黄铜火锅端上来了,下面是烧的发红的碳。味道果然不错,查尔斯熟练地用筷子夹起一片羊肉,放进滚开的肉汤里。这是我没料到的。看到我的惊讶的表情,他又故意炫耀一番。
“你学得这么快?” 我忍不住笑起来。
“我早就会用筷子了,我从小就爱吃中餐。我的东方情结从那时就开始了。”他透过火锅上升腾的热气看着我,他的眼神让我心里一热。
“真的?”
查尔斯看着我笑而不语。
坐在对面一直闷头喝老白干的中年人突然问我:“你是中国女人吗?”
我诧异地对他点点头,对他的措辞和腔调感到不太愉快。
“他是哪个国家的?”
“美国。”
“美国鬼子!他们太坏了!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
我吃了一惊,急忙说:“他是好人,他不是鬼子,他是朋友。”
那男人悻悻地说:“就因为他的臭钱?”
我有口难辩,我的脸涨红了。难道查尔斯就没有优点吗?再说谁知道他有没有钱啊。
“你们在说我#T#X#T#小#说#共#享#论#坛#吧?他不喜欢我,对吧?他说我是异族,是野蛮人?”查尔斯敏感地查觉出什么,他因自己给我带来的麻烦感到不安。
我摇摇头。我能告诉查尔斯这个陌生人的浅薄的言论吗?
查尔斯拿出钱包,把一叠钱放在桌子上,站起身拉着我离开了那家小餐馆。
上了汽车,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无辜,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但我预料只要我和查尔斯在一起,今后类似的事情一定还会发生,可能还有说得比这更难听的。难道这就是和他交往的代价?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他为在羊肉馆发生的事再三向我道歉,好像是他的错。“来,我们到‘鬼子’ 多一些的地方去。”从那天起,他就调侃地称自己“美国鬼子”了。
他带我到了一家燕莎中心底层的地中海餐厅,彬彬有礼的外籍经理站在门旁向我们问候,入座后查尔斯体贴呵护地为我介绍菜单。服务生热情地向我推荐菜单上的一道叫Artichoke Moussaka的主食,解释Karpathos Island其实是一道沙拉。
第三章 鸳鸯茶(4)
吃完饭,查尔斯送我回家。我的情绪仍然被那个人的话烦扰着,他打开汽车的音响,一曲节奏欢快的恰恰恰在汽车里回荡。
Picture you upon my knee;
Just tea for two,and two for tea;
Just 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Nobody near us to see us or hear us
No friends or relations
On weekend vacations
We won't have it known
That we own a telephone; dear
Day will break; you'll wake
And start to bake a sugar cake
For you to take for all the boys to see
We will raise a family
A boy for you
And a girl for me
Can't you see how happy we would be。
这就是他以前提到的《鸳鸯茶》的录音带,我明白了他说第二段和第三段“更精彩”的意思。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并不难猜。 但是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猜测。难道是我自作多情?
他开车把我送到我家楼下,临分手的时候,我和他道晚安。他握住我的手,一下把我拉到怀里。“你是个不愿受委屈的人,你生气的时候都那么可爱。”说完他在我的面颊上飞快地吻了一下。
顷刻间,我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转眼又到了星期天,他接我去他的公寓,说要给我做午餐。在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我他在看《红楼梦》,外语频道转播,有英文字幕。我好奇地问他是否喜欢,他耸耸肩膀,用一个模棱两可的动作回答我。他说林黛玉患有慢性精神忧郁症,应该去做心理治疗。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缺乏语言交流和情感沟通,这样的情侣会出问题不会长久。即使贾宝玉娶了林黛玉,以后他们也会离婚。他说古代中国人的“含蓄”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猜忌和误会。误会是情侣间常发生的事情,如果把事情阐明了,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我瞪着他一直等到他讲完,感到哭笑不得。他怎么会理解当时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他怎么会理解林黛玉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我跟他讲了半天也没什么用。
我们到了他的公寓,一所在燕莎中心当时为数不多的酒店式管理的涉外公寓,我惊奇地发现他会用中文对大堂助理说“你好!”,他还叫公寓里的女工“阿姨!”。
他住在第十层,是两房一厅的套间。一进门,我看到室内的陈设简单,色调协调,家具不仅安置得有条不紊,恰到好处,而且家具上一尘不染,没有一件零碎多余的什物。
站在客厅透过敞开的卧室门,我看到卧室里有一张硕大的床,上面铺着深蓝色的床罩,一对同样颜色的枕头整齐地安放在床头。
我从客厅“参观”到厨房,不锈钢的炉台和水池没有一点油污水渍,亮得耀眼。一切都像崭新的一样。水池边的案台上,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瓷砖铮亮。透过墙壁上碗柜的玻璃门,我看到一套西式的餐具整齐地排列着。
我又转回客厅,在一圈柔软的淡米色沙发上坐下。壁炉台上一幅放大的照片吸引住我。四个健壮的小伙子,皮肤被风吹日晒得发红,嘴唇上有干裂的口子,脸上带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右边第二个就是查尔斯。 他们带着太阳镜,穿着鲜艳的登山服,背着特大的双肩背包,肩膀上还绕着绳子和雪镐,脚下是起伏连绵的雪山,头顶上是湛蓝的天。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凑近照片仔细地看看。
“这是去年春天我们登上瑞涅尔雪山顶时拍的相片。”他从厨房出来,象变摩术似的端出两杯茶。
第三章 鸳鸯茶(5)
“瑞涅尔雪山在哪儿?”我端起茶杯暖暖手。
“在西雅图的西南方,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这些人是谁啊?”
“我们登山俱乐部的朋友。那是一次艰险的跋涉,我们还出了一点事故。”
“什么事故?”我忍不住好奇心。
“那次我们遇到了雪崩,我被埋在雪里,只剩头和一支胳膊露在外面。幸亏在我们前面有一块巨石挡住了滑坡的积雪,救了我们几个人的命。”他的口气就像说一件日常发生的小磕碰那般轻松。
我紧张地听他说完,才松了口气。“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纪录片,是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是一项艰险的运动,我记得他们快爬到顶峰的时候有人都用上氧气瓶了。”
查尔斯说:“登上珠穆朗玛峰是我的梦想。”
“登山是一项很酷的运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