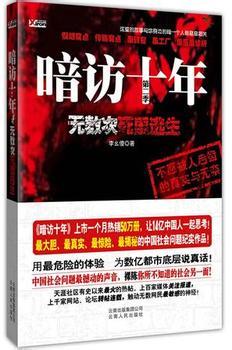暗访十年-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问,对方是什么人?
她说,那个男青年和她出生在一个村庄,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初中毕业,他们几年前就订婚了。后来,她出来打工,对方在家中种茶。昨天,她见到了小姨,小姨传话说,妈妈让她下个月就回家结婚。
我说,这多好啊。
她说:“结婚后,我就不能出来了,可是我不想回去,不想回到那个偏远的乡村,我想留在城市里。”
我当时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一样开导她,劝慰她,我说,现在也该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也该结婚了,你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结婚后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该有多好。
她用眼睛挖了我一下,问道:“那你为什么不结婚?”
我苦笑着说:“我这么穷,住在这里的鬼地方,一月收入勉强养活自己,哪个女孩愿意嫁给我。”
她低下头,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说:“如果有人愿意呢?”
我哈哈笑着说:“不会有人愿意的。”
那时候我真的很迟钝,我像一只从树上突然掉落路面的毛毛虫,我慢腾腾地爬行着,不知道有车辆辚辚驶来,不知道有狂风席卷而过。我按照自己的路线,慢腾腾地爬行着,不知道咫尺之间,骇浪惊涛。
我从口袋里摸出了一盒黄红梅,抽出一根,这是我经常抽的香烟。娇娘看到我想抽烟,从小坤包里取出一盒玉溪,塞到了我的手中,她说:“我早就给你买了,一直想送给你抽……这是真烟。”
我说:“这烟老贵了,要20块钱啊,你怎么买这么贵的?”
她没有接过我的话题,她好像在自说自话:“我这些年打工,积攒了10万元,我嫁给谁,不会给谁添麻烦的。我要开一间化妆品商店,一定能赚钱。我一结婚就不在这里干了,我要好好做正经生意。”
我真诚地说:“你很善良,又很能干。你男朋友娶了你,一定很幸福。我提前祝福你们。”
她突然不说话了,冷冷地坐着,场面显得非常尴尬。我说,这玉溪香烟果然很好抽,口感很好。她不言语。我又说,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她还是不言语。我没话找话地说,到了这个季节了,天气还是这么热,真想不到。她别过头去。
人在没有话说的时候,就会说起天气。我又无聊地说起了今天的气温,一会将要出来的太阳……
她没好气地打断我的话说:“今天要下雨了!”她站起身来走到门口。
我傻傻地说:“怎么会呢?你看这天色。”
她没有看天色,她只看着地面,噔噔噔态度坚决地走过走廊,走下台阶,走出了楼房。
现在,我明白了她当初在黎明时分来到我的出租屋,坐在我的床上,向我说起自己的过去,其实就是向我表白她的爱情。可是那时候我混沌木讷,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爱情发生在我和她之间。我当时已经年近而立,不名一文,潦倒不堪;而她当时才二十出头,泼辣能干,积攒了十万元。那时候的十万元,对我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我从来不敢想过会有故事在我和她的身上发生,我一直把她当成了小妹妹,活泼可爱的小妹妹。她的所有淘气和任性我都能够包容,我一直张开自己沾满鲜血的翅翼保护着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委屈。我没有想到,她居然会爱上我。
那时候我对她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她就像一个娇贵的瓷器,我双手捧着,我担心一使劲就会将她捏碎。尽管她发育成熟,生机勃勃,身材性感,可是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那个年代还残留着最后一丝纯真和爱情,这种纯真和爱情是与肉欲格格不入,而今天,爱情已经与肉欲水乳交融,无法分割。现在的爱情,与床铺只有一步之遥,往往几分钟就走完了过去几年才能走完的距离。
有时候我在想着,如果当初答应了娇娘,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人生有很多的无法预知和不可预测。
那天早晨过后,娇娘再见到我,就不和我说话,总是沉着脸。我也感到很难堪,不知道怎么哄她,才能让她开心。
这几天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画家去了西藏,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产,才凑足钱买了一张打折飞机票。我问:“你去了那里,没有一分钱,怎么生活。”画家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天无绝人之路。”
对于画家来说,西藏是一片圣地,那些没有污染的风景,随便割下一块,就能进入画布。这些风景让生活在工业污染和高楼大厦里的人们如痴如醉,画家去了西藏,也许会成功。
后来,他果然成功了。
思想家一如既往地穿行游说在学校工厂之间,让人们接受他重建信仰的观点。他就像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他和孔子一样屡屡碰壁,碰得焦头烂额。不同的是,孔子还有七十二弟子跟随,而他却是孤军奋战。
一家家学校拒绝了他,学校都在追求升学率,没有人会抽出时间聆听思想家的观点。一家家工厂的保安将他拒之门外,他们认为这个满口忠孝礼仪的青年脑子有毛病。在这个有钱能是鬼推磨的年代,傻子才会放弃金钱拾起信仰。
失败的情绪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思想家。
发布日期:2009…10…919:55:22
地老鼠手中玩弄着匕首,匕首在他的手中像皮筋一样绕着圆圈,他斜睨着我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们有缘,有见面了。小子,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端详着他,故意歪着嘴巴,装着一副傻傻的神情,我说:“你不是刘欢吗?哎呀,我们还在一起合影过?”
地老鼠恶狠狠地说:“去他妈的,别在老子面前装样子。小心老子一刀捅死你。”他又扭头对坐在座位上的一个青年用闽南话说着什么,那个青年站起身来,狐疑地望着我,他和地老鼠一样短小而不精悍。
那个青年问:“你跑到车上干什么?”
我的眼光越过他的头顶,穿过车前驾驶室的玻璃,望着远处点点路灯光。我的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神情,我幽幽地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
那个青年惊愕地看着我:“我问你为什么上我们的车?”
我继续装出一副傻傻的神情,继续用缓慢的语气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哦,哦……”地老鼠像刚下完蛋的母鸡一样,看着我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傻了?”
我依然用着刚才的语调说:“你吹送我如波如烟如云吧,我生是创巨痛深,我是血流遍体,时间的威权严锁于我,重压于我,我个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样的不羁。”
车上的闽南人都回过头来看着我,他们的眼睛中充满了惊异和疑惑。这些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不知道诗经和屈原,也不知道英国的雪莱。这些文言诗句,他们闻所未闻,他们即使“闻过”,他们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地老鼠将匕首架在了我的脖子上,他踮起脚跟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相信地老鼠只是在吓唬我,他只有胆量威胁我,绝对没有胆量刺杀我。我连他看也不看,望着窗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那个青年以权威的口气向车厢里的人炫耀着说:“这是一个神经病。”
我继续装神经病,我大声喊着“拉屎,拉屎。”然后就拉开了皮带,准备脱裤子。
司机过来了,他喊着:“谁把神经病带上车子了?谁带上来的?”看到没有人答应,他就摆着手说:“滚,滚,快点滚。真是晦气。”
我没有走,我装着听不懂司机的话,司机吓唬说:“快点滚,再不滚就要打死你。”他扬起手来,装着要落下去,其实不会落下去,谁会去打一个神经病人?神经病人让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退避三舍,因为神经病人杀人也不犯法,神经病人的外表让每一个人都深感恐惧。
我继续歪斜着嘴巴,侧着身子走到了车门口,身后不知道谁踢了一脚,我顺势就跳到了车下。我慢慢地走向小巷,偷眼看到身后跟着地老鼠和那个同样矮小的青年。
我装着没有看到他们,继续慢腾腾走上前去。他们要么是查看我的行踪,要么就是准备在没人的地方打我。我走到了小巷尽头,看到一户人家的门口放着一条矮矮的长凳,可能那家主人下午在门口聊天,现在还没有端回去。我跑前两步,一把操起长凳,抡圆了砸向跟在身后的地老鼠。地老鼠大惊失色,叫声哎呀,扭身就跑。另一个青年也急忙逃遁。小巷黯淡的灯光照着他们四条短腿,四条短腿争先恐后地移动着。我故意大声喊着:“老子今天砸死你们。”他们惊惶万状,呀呀叫着,像两只躲避劁刀的猪崽。
发布日期:2009…10…921:03:01
真对不起,重新发一遍——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走进假烟作坊,没有见到娇娘,她们说娇娘走了,回家结婚。
我当时很平静,我想当然地认为娇娘会幸福。因为他们青梅竹马,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在尽情渲染青梅竹马,都在说这样的爱情是完美无缺的。我当时甚至还在为娇娘高兴。
现在,我在电脑前打出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苦涩,我不知道这些年娇娘生活是否幸福,当初她不愿意回到乡村,而最后又被迫回到乡村,她是否收敛了自己的任性,是否满足于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此刻,这个静静的夜晚里,她在干什么?她会不会像我一样偶尔还能想起她?
又过了两天,我又要坐着长途大巴去闽南村庄拉货。
那天晚上,我刚刚走上大巴,坐在车厢最后一排的空座位上,突然一个人走过来了,手中拿着一把匕首。我惊愕地抬起头来,看到那是地老鼠。
地老鼠手中玩弄着匕首,匕首在他的手中像皮筋一样绕着圆圈,他斜睨着我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们有缘,有见面了。小子,还记得我吗?”
我仔细端详着他,故意歪着嘴巴,装着一副傻傻的神情,我说:“你不是刘欢吗?哎呀,我们还在一起合影过?”
地老鼠恶狠狠地说:“去他妈的,别在老子面前装样子。小心老子一刀捅死你。”他又扭头对坐在座位上的一个青年用闽南话说着什么,那个青年站起身来,狐疑地望着我,他和地老鼠一样短小而不精悍。
那个青年问:“你跑到车上干什么?”
我的眼光越过他的头顶,穿过车前驾驶室的玻璃,望着远处点点路灯光。我的脸上带着高深莫测的神情,我幽幽地说:“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
那个青年惊愕地看着我:“我问你为什么上我们的车?”
我继续装出一副傻傻的神情,继续用缓慢的语气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哦,哦……”地老鼠像刚下完蛋的母鸡一样,看着我说:“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傻了?”
我依然用着刚才的语调说:“你吹送我如波如烟如云吧,我生是创巨痛深,我是血流遍体,时间的威权严锁于我,重压于我,我个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样的不羁。”
车上的闽南人都回过头来看着我,他们的眼睛中充满了惊异和疑惑。这些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不知道诗经和屈原,也不知道英国的雪莱。这些文言诗句,他们闻所未闻,他们即使“闻过”,他们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意思。
地老鼠将匕首架在了我的脖子上,他踮起脚跟问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相信地老鼠只是在吓唬我,他只有胆量威胁我,绝对没有胆量刺杀我。我连他看也不看,望着窗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那个青年以权威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