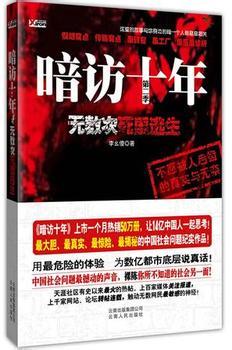暗访十年-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狗日的血头和打手,平时难得在厨房吃一顿饭,要吃就要吃猪肉,而我自从来到这里,还没有吃过一次肉。血奴们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次肉。
老哥卸完车上的食品,就蹲在房檐前抽烟,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他一张愁苦的脸。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老哥,递给了他一根烟。我悄声说:“老哥,带我出去。”
老哥惊讶地抬头看着我,不置可否。
我说:“老哥,你看,是这么回事情。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担心见不上一面。”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抽着烟,突然抬起头说:“中。”
我走进厨房里,厨师头喊:“灶膛烧红了,快点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默默祈祷着,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一只恶犬跑过来,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多了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恶犬摇着尾巴,把骨头叼在嘴上。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它们舒服地哼哼着,讨好地摇着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招手。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一只恶犬发现了我,呜呜叫着扑过来,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我吓坏了。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温顺了,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老哥一路蹬得飞快,耳边风声呼呼刮过,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冰凉冰凉。黑暗中,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我说:“老哥,换一下,我拉你。”
老哥说:“你蹬不了,这和自行车不一样。”
一直骑出了很远,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这才放慢了速度,说:“暂时没事了。”
我看着黑暗中的老哥背影,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为什么恶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说:“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报恩。我每回送肉的时候,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骨头分离。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我不让他们扔,带回给这些狗吃。你看,它们见了我有多亲。”
一道闪电,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惨白,接着,雷声隆隆响起,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雨声突然密集起来,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行,雨点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着电光,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借着闪电,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样翻卷着,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在野外度过雨夜,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剧《东方红》序幕的场景。
突然,一道闪电,打在了树上,也打在我们身上,将我们高高抛起,又轻轻摔下,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我惊魂未定,睁开眼睛,看到一绺树皮,从树顶到树根,被揭了下来,扔在我们身边。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像一柄蛇形剑,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哎呀呀,树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
我懵懵不懂地看着他。
“大蛇成精后,没处藏身,就藏在了老树里面,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来,每天都能吃饱。老树会有很多鸟落下来,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这些就够蛇精吃了。”老哥一本正经地说,“蛇精死不了,除非让雷电击死。这棵树里有蛇精。”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打雷闪电时,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否则会被雷击击伤击死。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那天晚上,我们躲藏在了树洞里,被大蛇发现,大蛇蜿蜒而下,想把我们作为美餐。突然,闪电来了,击打在大蛇身上,强大的电流也将我们轰出了几丈远。大蛇死了,而我们却安全了。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灯光闪烁,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坏了!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怎么办?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还是在抹雨滴。他也没有了主意。汽车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
发布日期:2009…8…2813:30:40
那是一辆绿色大卡车,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他们穿着迷彩服,有的手中还拿着短把冲锋枪。
我和老哥被带进车厢里,汽车冲破雨幕,继续向前疾驶。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知道,到了这辆汽车的车厢里,也就是到家了。
汽车开到那座院子门前时,已有一辆汽车提前到达了,院子的四周都布满了人,然后,院门打开,几只恶犬被厨师长拴在了柱子上,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粗大的链条被冲击得崩崩作响。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从一个个低矮的房间里带出了血奴,血奴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垂头丧气,还有的惊恐不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雨停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都有人,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从服装和神情上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他们是武警和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死亡了三个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经常会有人受伤,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但是,这次不同了,有三个人死亡了。而且,是被枪弹打死的。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将这些流氓包围了。突击审讯后,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他们便连夜突击,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
雨后的操场上,黑压压一片血奴,我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
天亮后,所有的血奴都被带到医院里进行血液检查,看是否感染了ai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说:“我是记者,我想见你们领导。”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记者?哪里的记者?”
我还没有回答,旁边一个血奴油腔滑调地说:“你是记者?那我就是省长了。”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血奴里什么人都有,我曾经听蹬三轮车的老哥说,有些血奴并不是生活所迫才卖血,他们是好吃懒做,自愿卖血的。还有些是逃犯,为了躲避追捕,就卖血。
我没有笑,也笑不出来,我对警察说:“我是xx报的记者,在这里暗访。”
“你的记者证?”
我拿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上级只分配了报社有限的记者证,全部被领导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关系的人瓜分了,在一线采访的记者都没有记者证。再说,即使有,我也不可能出来暗访的时候带在身上。
我说:“我真的是记者。”我走出了队伍。
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我再次向他说自己是记者,是来暗访的。那位领导很重视,他让身边一个武警带着我先回去。
来到了公安局里,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单位的电话号码、单位领导的名字、单位地址,一名警察拨打了报社的电话,然后让我在旁边一间小房间里等候。
我确定,他们相信了我的话。
午饭过后,报社主任来了,随同的还有报社的司机,他们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泪水盈眶。我也觉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样,泪流满面。
他们拿着报社的证明,把我领走了。
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轿车里,我的眼泪被颠出来了,那是幸福的泪花。我看着窗外,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是回城的道路,是回报社的道路,不是回血奴们居住的那座院子。我感到幸福无比。
后来听说,这些血奴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查出了几粒ai滋病,还抓到了一些逃犯。
长发只是外伤,身体没有大碍。那些流氓们都被抓了,还有的被判了刑。
曾经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彻底铲除了。
多年过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血奴群落,这个群落也不复存在了。
发布日期:2009…8…2814:41:29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会继续写,让大家免于受骗。
发布日期:2009…8…2821:21:06
谢谢各位朋友关注。
前面的都太沉闷了,下面写一个轻松的,酒托群落。
我可能也是最先注意到这一群落的人,那还是在2000年。
现在,酒托泛滥成灾,听说很多男人都被酒托骗过。
我揭露她们的骗人伎俩,给大家,尤其是男网友提个醒。
发布日期:2009…8…2823:08:51
【暗访酒托群体】
回到报社后,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过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能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户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