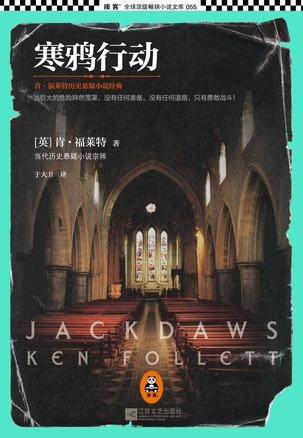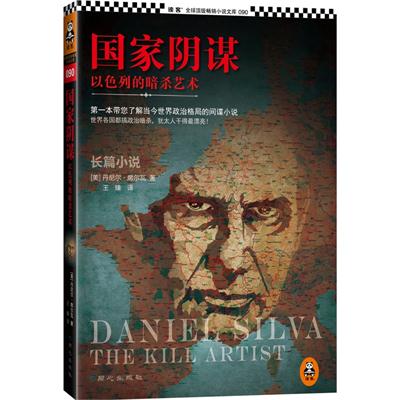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说他在罗马?”阿弗纳问道。十拿九稳了。从安德雷斯擦眼镜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十拿九稳了。“帮我找找他。”
10月3日早上,他们两个人搭乘德国汉莎的航班去了罗马。飞机落地之后他们租了一辆车,但安德雷斯只开到了距机场几英里的费米齐诺村。他们坐在离莫洛·莱万特不远的一家饮食店里,透过窗户,阿弗纳看见一群叽叽喳喳的海鸥在空中打着转,然后猛地向海里的垃圾俯冲下去。
一个矮小的年轻人来到他们的桌旁时,他们刚刚喝完第一杯啤酒。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浅色套装,系着领带,肩膀上搭拉着一件雨衣。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但皮肤却非常白,跟苍白差不多。据猜测,他可能是鞋厂办公室的经理,三十岁左右,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
“你好,托尼。”安德雷斯用英语说。
托尼面带微笑,点点头,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他飞快地瞟了阿弗纳一眼,非常中性的一眼,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友好。但即使他没开口,阿弗纳也能感觉得到托尼是他登梯的第一步。无论他有用与否,托尼毕竟是另一个同盟。“你们点菜了吗?”他问道。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意大利口音,但很流利。“我饿死了。”他扫了一遍菜谱,把要的菜告诉了服务员,要酒的时候非常谨慎。阿弗纳看见他已经有了一点肚子。他的眼里充满了智慧与嘲讽。托尼没有扮演什么角色或任何伪装的成分。
“阿弗纳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谈过的那个朋友。”等服务员把他们的午餐端上来之后,安德雷斯说。“我们,当然……就是他有问题要问你。”“好。”托尼说。他不慌不忙地吃起来,显然很满意他的午餐。“现在在阿拉伯人的圈子里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招募之类的活动。特别是有一个人的活动。”
阿弗纳感到毛发直竖。托尼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下,又轻轻地向上抬了抬,好像在问:“难道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吗?”
是的。没必要转弯抹角。“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阿弗纳问道。
托尼揩了揩嘴巴,又拭了拭嘴角,然后把餐巾放下。“你这就谈生意了。”他说。
一时间他们都不说话了。安德雷斯看着阿弗纳,然后转向托尼。“喂,我保证给钱。”他说。“你不必担心这个。但你知道的,阿弗纳必须知道你提供的东西他是不是感兴趣。这公平吗?”
安德雷斯说这番话的时候托尼一直看着阿弗纳。然后他点了点头。“兹威特。”他毫不迟疑地对阿弗纳说道。“那个人的名字是兹威特。”他说得很快,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很难听清楚。
“威尔·兹威特。”阿弗纳立即说。他说得很快,就像说一个密码一样,为的是不让安德雷斯听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个密码。他是个软目标,就在这里,罗马。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是四号。毫无疑问,托尼指的就是那个人。
托尼也一定在这样想,因为他啜了一口酒之后,问道:“好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
阿弗纳想了想。“五天之内,”他说。“你能搞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日常安排吗?他住在哪里?他去哪里,什么时候去?去见谁?我们对这些感兴趣。”
询问这些信息并没有泄露什么。出于很多原因都可以这样问。安德雷斯介绍阿弗纳时说“我们中的一员”,就是说,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中的一员。不同集团的人会经常互相留意彼此的活动。恐怖分子也许希望清楚地知道在一次联合行动之前另一个组织不会渗透进来,或者怀疑像兹威特这样的主要组织者也许会靠近他们,做一个双重身份的特工。在地下活动中,监视别人的活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好。”托尼回答道。“五天可以。你出的价是五万。”
阿弗纳站起来。“五天后,”他说,“安德雷斯会在这里把钱给你。”
在飞回法兰克福的途中,安德雷斯热情有加。“你认为托尼怎么样?”他不停地这样问。“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非常激进的一个人,来自米兰。但他从不谈政治。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很多年了。”
当天晚上,在跟同伴们见面的时候,阿弗纳提出了一个渐进的行动计划。无论是在那份名单上还是在时间上,他们都把兹威特提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0月8日,除斯蒂夫外,全体队员移师罗马。他要飞往西柏林核实与主要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来自卡尔以前的一个阿拉伯线人,他是“穆萨德”雇用的几个固定的联络人之一。)如果线索证明可靠,他们就会暂时放弃兹威特。如果不可靠,斯蒂夫就来罗马跟他们会合。
阿弗纳与托尼的第二次见面是第二步。他要带着安德雷斯一同前往。但没理由让安德雷斯见其他的人。如果托尼的情报带来了第三步,阿弗纳就甩掉安德雷斯,只告诉他,自己需要的东西暂时都搞清楚了,以后会和他联系。
第三步就是让托尼的负责监视的人带着他们进行模拟突袭,至少两次,但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说,托尼的人开车带着阿弗纳的人(卡尔除外)去突袭现场,再从现场回来,全程使用预先安排好的一套暗号,好像监视是这个演习的全部目的。(在监视一个经验丰富的可疑对象时,参与的人多达十几个是正常的,把被监视对象从一个监视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行动开始前,把托尼安排的袭击前的监视人员撤走,只留下袭击后帮助逃离的人。即使如此,他们离现场最近的人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在实际突袭时不能有外人在场,他们要等看到或者听到新闻之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之后,因为自己与这件事有牵连,所以不会跟别人讲。即使讲,也讲不出什么东西。
第一辆帮助他们逃离的车子必须由阿弗纳的人安排。这辆车子要把突袭的人,无论是谁,带到等着的第二辆车上。然后,卡尔独自来“清扫”现场,以后再和其余人员会合。
如果他们能走到第四步,那第四步就是突袭。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根本不必做任何改动。托尼的汇报非常仔细,阿弗纳指示安德雷斯把五万五千块的一半用崭新的百元美钞付给他。然后让安德雷斯飞回法兰克福,再安排他跟托尼单独见面一次。
这个意大利人没有提什么问题,同意继续监视兹威特。这时阿弗纳的人也参加进来。他也同意在罗马附近给他们安排一套安全屋。托尼提出做这件事要增加十万。这似乎合情合理。这样,在斯蒂夫跟他们会合之前他们就“彩排”了一次。
斯蒂夫关于萨拉米的消息证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汉斯称它是一个“谣言”。这个词汇是阿弗纳满怀热情地从法国报纸上学来的,意思是虚假的流言——于是突击队又进行了一次暗杀兹威特的演习。这一次,斯蒂夫也参加了。每次彩排,托尼安排的司机都不同,但监视员不变。兹威特是个非常合作的目标。他的日常安排,即使在每个细节方面,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被害人对害他的人给予的最大的帮助。
在突袭之前的这段时间,他们的食宿由他们自己安排。卡尔坚持这样做,因为这样安全。托尼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他的人只是到预先安排好的大街上的某个地方去接阿弗纳和他的同伴,彩排完之后把他们放在另一个地方。(后来阿弗纳渐渐相信,尽管他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托尼还是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在罗马找到他们。整个城市似乎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托尼和他的人暂时见不到的惟一一个人就是卡尔。他总是躲在隐蔽的地方,看有谁跟在托尼的监视员后面监视他的监视员。他还要准备备用逃离路线、安全屋和证件。他是突袭队的安全网。如果哪里出错了,只有他才有机会看出来,并向其他的人发出警告。
突袭之后,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卡尔第一个到达现场。他要处理任何跟他们有牵连的东西,甚至提供假线索。他要把第一辆帮助逃离的车子停到另一个停车场。他要搞清楚官方在现场的所思所想,或者初步调查和追击的方向。
所有这一切都使卡尔成了一个大忙人,也成了最容易暴露的人。
到10月13日,只剩下那辆帮助逃离现场的车子悬而未决了。他们其中一人,也许是斯蒂夫,开一小段路之后,要把车丢在现场附近。很显然,这样的一辆车不能是托尼的人登记的。可以是偷来的,但似乎不用冒这样的危险。而租车又会浪费一套证件,而且在租赁处还要把托尼的一个人或者阿弗纳的一个人的资料登记下来。
“我们还需要一辆车。”阿弗纳对托尼说。“一辆也许要扔掉的车。”
就像他以前接受他们所有的要求一样。他们坐在那佛纳广场附近的一家路边咖啡馆里,继续用勺子舀着冰淇淋。“可以安排,”他回答道,然后说了一家美国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及其一个分部的地址。“他们会给你租一辆外地车牌的车子,不必担心证件的事。如果警察去租赁公司调查,他或者她会告诉他们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得克萨斯人拿着一张‘晚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在米兰租的。不过,你要出一万块。”
他感到吃惊。
“但你不是欠我的。”托尼继续说。“我给你一个巴黎的号码,你下次到那之后,打这个号码,找路易斯。告诉他,我告诉过你你欠他的东西,付给他就行了。不用着急,一个月之内就行。”
这很有趣。难道托尼也有老板?或者有个合作伙伴向他收取在罗马活动的特许费?或者仅仅因为他欠“路易斯”一万块而让阿弗纳给他带去,省去了自己亲自飞往巴黎的麻烦?
或者,就像卡尔听说过这件事之后若有所思地说的那样,难道是个陷阱?但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的第六感觉没有向他发出警告。
在国际间谍、国际走私、国际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武器交易商、线人和其他私掠者。有时候,他们形成比较松散的组织——一个互相联络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如果他们提供不了顾客需要的服务,就把顾客转给其他人。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动机,其余的则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钱。只为一方服务——尤其是那些地下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总是在快速地变换同盟者——一般来说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不过,交易商们会在某项活动或某件商品上划一个界限——有些人也许从来不碰毒品或弹药,有些人也许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有些人并不是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工作——他们通常会给所有愿意出好价钱的顾客提供信息和服务。然而,至少从短期来看,私人侦探或其他合法商人不会把顾客卖给另一个人,他们也不会。“无论托尼怎么想,或无论他怀疑什么,”阿弗纳对卡尔说。“他都知道我们付给他的钱是干净的。”
还剩下一个问题,用行话来说就是“谁和什么”的问题。这只与四个人有关,因为卡尔的工作总是一样的。斯蒂夫无疑是最好的司机,所以那辆逃离现场的车子由他来开。按照以色列军队的传统,作为领导,阿弗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