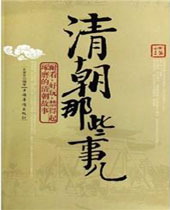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去把她身上的绳子解开,接着她就恢复过来,跟着那个人一道离去,然后在寂静的夜色里回家。有时候我一路过小校花家的后窗,就觉着要是走近窗户,再从窗帘上那个小破洞往屋里一看,就会看见一盏彻夜通明的灯光里,刘老师一身溜光被户籍民警铐在床上整。
我爸说户籍民警太差劲,过那么久了还没把姥姥的户口转到成都来。又说该死的老保守还在四处活动,不然的话,他早又带我外出钓鱼去了。
我妈以为我还想着要跟我爸去钓鱼,就说要带我进城去吃回锅肉。
她说的那种回锅肉三毛钱一大盘子,红亮红亮的,又香又辣又有点甜,蒜苗又绿又嫩,吃一口油会流到腮帮子上,好吃得要命,我和她两张嘴也吃不完一盘。只是我知道,要想跟我妈进城吃到回锅肉,要费好大的事才成。因为她每次进城,虽然凌晨四五点就要起床,但要磨蹭到上午十点才能出门,最后要磨蹭到晚上八点才能回家,而买回来的东西顶多是两尺布,要不就是一个水瓶塞,跟回锅肉根本不挨边。
她看着我说,不想跟妈去啦,老三?
见我不吱声,就对全家孩子大声说:
你们谁想跟妈进城吃回锅肉?就是明天,礼拜天,谁想去?
好一会,没一个孩子答话。我敢说,我们全家孩子没谁不想跟我妈进城去吃回锅肉,但又没谁敢。要是我爸也一起去还差不多,因为靠着他那个急性子,还没进城就能让大家早把回埚肉吃到肚子里了。我找到我爸问他去不去吃回锅肉。他正坐在小凳子上洗脚,猛地抬起头来说:
我?您饶了我吧。你妈那个慢性子,吃一顿饭的碗筷锅勺,能洗上半天工夫。跟她一起去吃回锅肉?得,您快另找高明吧。
我爸真是少有的谦逊之人,管我叫您。
我说,你不一起进城,是不是想一个人去钓鱼?
他说,没错,我一直没忘了那条被放跑的大鱼,多精神的的一个老头啊,我得去会会他,没准他也一直惦记着我呢。您呀,就进城去吃回锅肉吧。
我说,你说的是那条大鱼还是那个老头?
他说,管他呢,都一样。劳驾,去把擦脚布递给我。
我把擦脚布取来给了他,他擦完端起地上的盆去厨房倒水,脚下踏拉着鞋。他这人其实不发脾气时人挺逗,对孩子一律称您,遇上更谦虚时就管孩子叫老祖宗,还说劳驾。
我妈又拉着我说,看看你都瘦成啥样了,明天星期天,跟妈进城吃回锅肉去,啊?
我说,那你别太磨蹭,我才去。
她笑了,说行,妈来个动作快。
但是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我跟着她在屋里到处转圈,已经累得不想再去了。从清早睁开眼睛开始,我就一直在跟着她满屋子转。家里的房子是两间,还与邻居共用一个厨房,幸好加起来总共就二十来平方米,要是屋子再多些大些,不知我妈还会有多少干不完的活。
她一会擦锅台一会又擦锅台,而家里就一个锅台,其中有一半还是人家的。
我就说,妈,还没擦干净,再擦擦吧。
她说,擦两遍了,该干净了。
我暗自高兴,心想一直到出门前这该死的破锅台不会再耽搁我妈了。
我妈又擦了一把饭桌。当然不是只擦一把,而是左手提着右手的袖子,右手抓着抹布在桌子上用力使劲来会擦,好像饭桌脏得不可想像。我站在桌边看桌子,简直不明白这张每天擦好多遍的桌子,她刚才擦了一遍干嘛又要来擦一遍。
我说,妈,你看桌腿,再擦擦桌腿。
她说,刚才已经擦过了。
我说,再来几下嘛。
她就真又擦了一会桌腿。
我说,妈,还有这儿,桌腿的底儿。
她说,那怎么擦呀?
我说,把桌子翻过来,四脚朝天擦呀。
她说,行了行了。
我松了口气,谢天谢地,桌子也算完事了。
看情形我妈该出门了。但一转眼她又进了厨房,我赶紧跟在后面。
她把菜板放在水龙头下不停地冲呀冲呀,边冲还边用竹扫帚反复刷洗。那种刷法是把竹扫帚在菜板上有节奏地搐几下,然后刷几下,又搐几下,刷几下。我就守在水龙头前,小声说行了吧,行了吧。生怕说大声了惹她过一会又来刷一次。
家里人把我妈的举动闷声不响地看在眼里。全家人都知道,我妈是那种越临近出门越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仿佛在临出门的那一关头,她能想起天下所有的事情来。而且一旦那所有的事情不在出门前一下子做完,就好像再也来不及了。家里人还知道,每到这个火候上,再急也没用,有火都得在心里压着,千万别催她,否则她会想起天下更多的事情来,就别再指望出门了。
其实我爸比我妈更要命。虽然他并不进城,但他要去钓鱼,要送别走了我妈和我才放心,因此一直守在门口,边看手表边催我妈,那种急得要死的样子简直像要把谁给宰了。他冲我妈说你看都几点了,还不出门啊?而我听见他已经这样说了好几个钟头了。要在往常,差不多每逢我妈出门,我爸演的都是这种守门催叫的角色。但我妈好像故意对着干一样,我爸越催她越磨蹭,有时还急吼吼地用保定乡下的一种骂法骂我爸催死报命。这种情况让姥姥也气得干瞪眼。她坐在床边上冲我妈说忒能磨蹭,忒能磨蹭!怎么就这么能磨蹭呢?
用姥姥家乡的说法,那个星期天早上,我妈千真万确一直在捅鸡摸(猫音)鸭儿。
不过我相信她很快就要出门了。
但这时候她却更忙了。
她又去擦了一会锅台,又去冲了一会菜板,又去擦了一会桌腿。老天作证,后来她真的叫我帮着掀翻饭桌,擦了擦桌腿的底儿。我爸急得来回快步走,简直急红了眼,要不是大哥二哥拦着,他差点自己跟自己干了起来。
不过我相信无论如何我妈也该出门了。
没想到她又抱起床上的小弟弟,蹲在床边往地上的盆里把尿,嘴里还嘘嘘地吹响。六弟不满半岁,几哩哇啦叫,好半天也尿不出一滴尿来。而我爸怕就怕这个,他早已提前给小弟把过好几回尿了,最后一次还被小弟用没长牙的嘴给咬了一口。但这时候,我爸已经被气跑了。如果不是因为年岁大了点,没准背对着我们坐在窗前的姥姥会被气得从窗户跳下楼去。
之后,我跟着我妈终于出了门。
但是看样子,这还不能算真的出门。因为她显得有心事,完全没有进城那种轻松劲。果然,没走出半里地,她叫我原地等着,说要上一趟厕所,说完就小跑着回家去了。
可能没人知道我妈这种慢性是怎样形成的,又算不算一种本事,姥姥也未必清楚。一年前,我妈带我回她的老家保定,回返的那天上午,叫我在母子候车室守着一大堆东西,说她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她的影子转眼不见了,我的脑袋很快就晕晕乎乎。我守着老家人送的装着棉花、被套和新棉衣的一个个大包小包,仔细听着车站广播,但听不懂喇叭里的女人说的是些啥,只知道说的是火车的事。因为每广播一次,候车室里的旅客就像听到通知一样,一批一批地急忙走出候车室进了站台,最后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只剩下了我一人。老不见我妈回来,我心跳加快急得不行,生怕我们要坐的那趟车来了。后来我急得睡着了,我妈才突然推醒我,风风火火地背起东西就小步跑,上了早已到站马上就要开动的一趟火车。在车上,我怪她一去就不回来,差点赶掉火车。她说没关系,铁路职工每年每人两张火车免票,我爸和她的加起来就是四张,那种免票上哪儿都行,就是赶第二天的车也成,不用急。我说那么长时间你干啥去了?她说买针。我说买针也用不了好几个钟头呀,更用不着偏偏要赶车的时候去买呀。她说保定的针好,不然在别处就别想买着。
原来是保定的针好呀?
不见得,老家的针好。
保定不是老家吗?
是呀,保定的针好。
说来说去还不是保定的针好。
是呀,但是保定的针不好。
又不好啦?
你爹把保定的针做了鱼钩,我缝衣服哪儿也找不着针。
保定的针能做鱼钩?
能呀,鱼一咬,钩就直了。
可能因为我爸做鱼钩时,火候没把握好吧。
管他呢。反正钩一直,你爹就钓不着鱼,就会钓起个老头来。
连鱼都钓不了,还能钓着老头?
你爹把钩提起来,离水面三尺高钓呀。
那就更钓不到老头啦。
钓三年就能钓着。
这不是瞎说嘛。
你爹这样说的,没准不是瞎说。
我妈一年前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她就照样小跑着,回到了我等待的地方。这一回,她虽然累得直喘气,但样子的确是愉快的。
我说,你昨天说你要来个快动作,这就是快动作呀?
她说,我就是当时太快了,你爸爸才捅了漏子。
我说,你说啥?
她说,啥?哼,我一直不想提这事,还老逼我。
我说,我爸逼你啦?
她说,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样,还不改。
我说,你倒底在说啥呀?
她说,你不知道,你们几个孩子都不知道。从前小校花她妈妈跟她爸爸在外面搞破鞋,就因为我当时那个麻利劲,没叫住你爸爸,他才去捅了漏子。可现在倒好,你爸爸还不长记性,干啥都还是急吼吼的。
我妈说的话让我干瞪眼,她这人就爱这样好像憋了很久才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吓人的话,但要问追根问底弄明白,就别再指望进城吃回锅。
第十二章 一九六五年母亲丢了两分钱
我们从铁路局围墙外的人民北路路口出发,往城里走。要是坐电车进城,买票要花四分钱,我妈从来就舍不得。大马路两边没有商店,只有叶子老大的法国梧桐树,还有老高的土墙,墙顶上盖着青瓦,有点像那个很出名的文殊院的院墙,只是墙上没抹成朱红色,单就是土色。一直要走到名字响当当的骡马市才看见路边有了店铺,这就算开始进城了。我妈自己有只手表,但从不戴在手上而是装在裤兜里,我拉着她的衣角问怎么还不吃回锅肉啊?她就拦住过路的人,问人家几点了,然后对我说咱们刚进城,时间还早得很。我不懂我妈说的时间还早得很是啥意思,只知道每次在城里,至少要等我问上二十多次,才能到吃饭的钟点。因此我认为我妈就是时间,她说时间到了那就时间到了,她要是等到天快黑了,照旧说还早得很,我也没办法。我最恨的就是吃回锅肉要被时间管着。而且,跟我妈进城次数多了,我已经摸清楚要在城里先吃了早饭,等什么时候再饿了才能吃上回锅肉。我就说,妈,都十二点过了,咱先吃早饭吧,不然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轮上吃回锅肉啊。我妈就带我找饭馆,买那种八分钱一碗的葱油面条。
一次,我们迷失方向找到城边上,看见了挂着担担面招幡的面铺。面铺是老式的破旧平房,爬立在一条不宽的破烂柏油路边上,木板墙青瓦顶,屋沿下的招幡蓝底白字,屋后面是大片没长出庄稼的农田,吃面的人多得没地方坐就立在门外,要不就蹲在路边上,手端着碗吃。吃面的人多是些拉架架车、黄包车、推鸡公车、修自行车的,大冷天都光着上身,被辣得满头大汗,不停擤鼻涕,乱七八糟的各种破车停在路边上。我和我妈也是站在路边上吃的,小小的一碗担担面,上面是豆花、酥黄豆、炸花生米和碎咸菜头,底下才是面条,淹在红油里,吃上两口就辣得直喘气,恨不能用刀把舌头给剁了去。那大概就是几十年后闻名天下的成都担担面的发源地。
肚子饱了,又去逛城里。走着走着我妈就一副很纳闷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