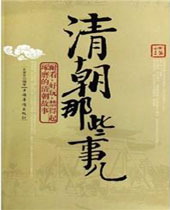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还没教会我。这几天我连个鱼毛也没钓着。
你呀,跟他能学到什么呢?你爹钓了十几年鱼,少说也把咱家的米抓了上百斤喂鱼,可从没见他钓回家一条鱼来。你想钓鱼,只要别让鱼把你给闹到河里去,就比什么都强。其实呀,你爹钓鱼也挺累的,他往河里扔的那些粮食也不算啥,鱼们吃了还不是吃,咱们少吃点,省着点就行了。再说啦,从前有个人呢,站在山上用车竿往下面的大海里钓鱼,用的钩有好几个人大,线轱轳有火车轮子那么大,用的鱼饵是五十头小牛。那个人钓了三年也没钓着个鱼毛,三年后窝子发了,就钓起来一条大个儿的。那天,大鱼吞了钩,拉着鱼线直往海底奔,又往海面上蹦,整个大海一下翻了天,几千里地外都听得见,甭提有多热闹了。
你亲眼看见了,姥姥?
我成天不出门,哪儿看得着呢?还不是你爹说给你妈的听,你妈又告诉了我。没准你爹看见了。孩儿啊,以后你爹要再揍你,你就认个错,要不就往死里哭,你老是不吭声,哭也不哭一下,你爹又狠,连日本人都敢闹,打球也用的是左手,拧着你多不是滋味啊!
姥姥边说边揉我被拧过的屁股和大腿,那些地方肯定又是青一块紫一块了。她还换着手揉自己的屁股和大腿,好像她也被拧过,我忽然记起多年前那张大饼,想看看姥姥的伤,叫她撩开后腰衣服。她说正好可以给她抓一抓,就立在地上,上半身趴在床上,露出后腰。姥姥的腰看上去能看到骨头,瘦得不成样子,一个锅盖大的红疤留在后腰上,仿佛十多年以后我下乡当知青时才见到过的那种在公社盖的大红印章
姥姥说那里老痒痒,每天夜里都要抓才行。我就轻轻给姥姥挠痒,边挠边问她,那次那张大饼最后谁吃了,姥姥没答话。我又问,她才说:
那张饼,我当时还以为全喂了你爹,可晚上听你妈说,你爹把那张饼偷偷给了楼下那个刘老师。
我说,怪不得一跟我说刘老师,我爸就那种想吃人家的腔调,他是喜欢刘老师吧?
姥姥说,你爹叫刘老师把饼给小姑娘和她哥哥吃。
我说,她为啥不让咱们家的人吃,非给了人家?
姥姥说,嗨,你爸爸欠人家刘老师。
我说,欠钱?
姥姥说,钱倒是不欠,你爹你妈俩人都上班挣钱,比刘老师家强一点。
我说,我不信,咱们家人多,她们家人少,也是俩人上班挣钱。
姥姥说,刘老师上班只有十几快工资,户籍民警又不疼两个孩子,灾荒年那阵常挨饿。
我说,当老师就挣一点钱?
姥姥说,学校里别的老师,都比刘老师挣的多得多。
我说,她招惹谁了?
姥姥说,好了,少管别人的事,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我肚子太饿,想起铁中食堂卖的五分钱一个的卤兔头,就向姥姥要五分钱。姥姥明白我的心思,二话没说就起身走到她睡觉的床边上坐下,然后掀开旧棉花床垫伸手往里摸,摸出了一个小包,边打开边说:
孩儿啊,姥姥就剩下八毛钱啦,咱们说好了,只给五分,啊?
我点点头。她又说:
这点钱都是姥姥从你爹挂在门背后的上衣口袋里掏的,每次掏五分八分的,你爹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个人,兜里有多少钱,从来就没个记性。
说着,她从手绢上的一小把钢崩儿里找了个五分的给了我,又说:
你可不兴掏你爹的口袋,啊?
我又点点头,心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谁比姥姥更疼我了。
第十章 每天半夜把她铐在床上堵住嘴整
一出门,我叫上小校花一起去铁中买兔头。
自从刘老师出了事,楼里楼外再也没孩子跟小校一起玩,要不是我爸说过等她长大了要把她弄回家才算有本事,我也不会跟她玩。但是走出去不远,她又不想去了,我说不去算了,等买了卤兔头我一个人吃,她才又跟了上来。我问她坏人找到没有?她说还没有。
你爸是公安,还抓不到坏人?我说。
我爸好像不喜欢我妈,经常整我妈。她说。
我爸有一次说,有个女的被糟塌了,好像指的就是你妈。我说。
我爸每天半夜整我妈,用手铐铐在床上,用毛巾堵嘴,我妈喊都喊不出来。她说。
你们不帮你妈?我说。
里屋门关了,我和哥哥进不去,只能在外面屋子听。她说。
要是我,就把门砸烂。我说。
我哥砸过,我爸一冲出来就打我哥,有一次连裤子都没穿就冲了出来。她说。
我要是你妈,就到单位上去告你爸。我说。
就是,但我妈每次半夜挨完打,一到白天又没事了,还跟我爸说话。她说。
你妈是不是只挣一点钱回家?我说。
不知道,反正我妈在家就抬不起头来。她说。
我爸说你爸爸是两个人。我说。
是啊,我爸白天一个人,夜晚就变成另一个人。她说。
到了铁中食堂,不想早关了门,大师傅们正在吃饭,但还是卖给了我。一出食堂门,我把兔头掰开给小校花一半,自己留一半,两人边走边吃。小校花的模样有点可怜,让我老想起她妈妈跪在河边的样子。她好像有点怕她爸爸,也有点怕她哥哥。她说卤兔头真好吃,但她爸爸从不给她零花钱。我正要说话,小校花的哥哥从前面走了过来。
小校花的哥哥一向少言寡语,我好几年没看见他脸上有过什么表情,更别说笑容了。他把妹妹叫到一边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朝铁中围墙侧面的小路急匆匆走去,像风一样轻。等哥哥一走远,小校花把没啃完的卤兔头往旁边地上一扔,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把我一人扔在半路上。我很不快活,但心里想,我爸和我把刘老师从沙河里钓了上来,一定是她哥哥刚才跟她说了我什么坏话。还有,她哥哥的去向也让我不好受,那个方向正好通往西北河,我就是走那条路去河边钓鱼,被老保守的那个小野种抢跑了鱼竿。
到家门口时,我爸正在楼下空坝上修他的自行车。那破车也是一辆谦逊之车,不管怎么折腾从来不散架。至于有多破,反正算得上世界上最破的一辆,每次都能摇摇晃晃跑老远的路,顶多快要散架了,才把我爸的手呀腿呀狠狠叫几下子。虽说这样,破车却能带着我们找到成都每一个钓鱼的去处。
到了晚上,我爸带我出门去逛夜市,好像根本就没揍过我,我可从没见过脸皮有这么厚的人。夜市上人很多,到处挂着明晃晃的灯泡,我爸说我想吃什么只管说,他给买。我没吭声。在沿街排成溜的手推车上,有切成短节的甘蔗码放在大玻璃罩里,穿白上衣戴小白帽的师傅对买主笑嘻嘻的。甘蔗刮过皮,每个结还给削去了一圈,干干净净的。推车上什么吃的都有,还有大鸭梨,谁买,师傅马上就用刀削皮,动作快得好像眨眼工夫就能削好一个,而且皮削得比纸薄,中途不削断。我爸就乐滋滋地说:
瞧,这手艺,甭提了!
我听了嗓子眼直发干。
看见师傅转眼间就把一大团面给拉成了贼细的面条,我爸就说:
瞧,这手拉面,再加上点黄瓜条和芝麻酱,就盖了帽了!
我咽了咽口水。我爸又说:
身上拧的地方还疼吗?
我把头拧到一边,不理他。
忽然,在凤凰山鱼塘放走我爸那条大鱼的省武术队的小伙子,从前面朝我们奔过来。
哎哟,师傅,想不到在这碰上你们了!小伙子笑着高声说,还想拉我爸的手握。
我又不是什么海灯法师,谁是你师傅?我爸说,把手一甩,不想握手。
哎呀,看你说的,至少你是钓鱼的师傅呗。对方说,挺当真。
怎么,凤凰山不好玩,又跑到这来玩了?我爸冷言相对。
不是,师傅。我退役了,分到你们铁路局上班了。来来来,咱们找个馆子喝两杯,我请客,也算陪个不是。小火子说着又拉我爸的手,样子又高兴又激动。
我爸推辞说不去,对方连推带拉硬要他去,我爸一再推辞,嚷嚷起来:
你没看见这个时间,全国的饭馆都早关门了吗?上哪去找什么饭馆!
我爸这一嗓子,惹得周围有好些人都看他,有几个还凑上来,以为他在跟人吵架,其中一人马上要开口劝架了,他还在扯着破嗓门高喊。
那明天,明天中午,好不好?小伙子说。
我在电报所上班,你发个电报来就行。我爸说。
电报?我不会电报,我给你打电话。对方说。
行。我爸说。
说好了啊,再见!小伙子说,边摆手边转身。
忘不了!我爸大声说。
我拽了他一下说,小声点。
他回头一看周围的人,照样大叫说,怕什么怕,老子又没抢人!
人们散开后,他又带着我四处转,逛了一阵后说:
我早就知道有个省武术队的分到了我们铁路局,那封电报是我抄的,但我不知道会是那个臭小子。明天中午看我怎么吃他一顿,到时候你也一起去,可不能便宜了他!
我说,你就不能小点声?
他说,怎么小得了声?你小子可能还不知道爸爸的大嗓门怎么练出来的吧?不知道是不是?告诉你,这个解放前,我跟日本人学电报那些年,一不留神就挨揍。每次揍完了,日本人就命令我穿着裤衩站在雪地里大声背诵密电码,背错一个码就会被立即开除,每次都背三个钟头,背得满头大汗,不能出一点差错,爸爸的大嗓门就是那个时候给练出来的!
回家的路上,我说起了午后小校花讲的她爸欺负她妈的事。
小丫头咋说的?他说。
说把她妈铐在床上堵住嘴整。我说。
小丫头看见了?他说。
没有,隔着门听见了。我说。
我又把她哥哥从铁中围墙侧面走远的事也说了出来。
那条路不是平时常有人走吗?我爸说。
现在又没到游泳的时候,那条路根本没人走,两边上的荒草都爬到路上去了。我说。
是不是那小子在找啥?他说。
我那次去河边钓鱼被老保守那个小野种抢了鱼竿,就是走的那条路。我说。
你怎么不早说?他说。
我这不是在说吗?我还一直在想我那副鱼竿。我说。
你那破竿值几壶醋钱,要紧的不是这个。我看,咱们得快点回家。他说。
你又想去跟户籍民警报告?我说。
我不上感着他,就别指望你姥姥的户口要早日迁过来。他说。
姥姥说你欠人家刘老师什么东西。我说。
这个老娘们,怎么这样说话!他说,自己先走了。
晚上,我在床上睡下很久了,我爸突然跑来小声叫醒我,叫我快穿好衣裳,说他刚才下夜班时发现有个人像老保守。然后,他带着我溜出家的后门,穿过菜园子,几步到了铁路局大礼堂门外的场坝边上。夜场电影已经开演,大门外没剩下几个人,我爸把我拉到身边,躲在树下注视着那几个人影。他说只要看准了老保守,马上就去把户籍叫来抓人,但好一阵也没看出老保守在场。后来,他叫我进礼堂去看一会电影,自己仍在树下监视老保守的踪影。我爸跟老保守较上了劲,但他说自己上感户籍民警是为了姥姥的户口,实际上最先的情形的确如此,但不久后他和户籍民警各自都横添了一个共同对付老保守的压力,而这些在那时候,我和小校花都蒙在鼓里。我只记得那天演的是抓特务的电影,特务用手铐把一个女服务员铐在床上,用毛巾堵住嘴不准她喊,好像小校花她爸整她妈一样。
第十一章 苦涩年月的一点幽默
刘老师死了,但老保守仿佛仍在什么地方出没,又让人觉得刘老师仍然活着。有时候我想一人再去那条沙河边走走,就怕刘老师会依旧扑跪在岸边,怕有人走过去把她身上的绳子解开,接着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