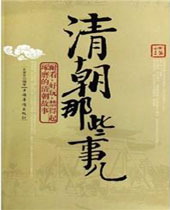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车师傅,我穿过街道,走进工农兵商场,去找那个在马道商店呆过一阵的胡涂。说不定,那个胡涂真是当年在成都火车站背后每天给老保守送饭,又在西北河边抢走过我鱼竿和帽子的小杂种。
工农兵商场是西昌城里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场,一位柜台服务员听我打听胡涂,抬手指了指不远处一根大柱子旁边的一个柜台说:
好像他去开啥子鸡八巴诗歌会去了。
又问一个女服务员,她照样指了指那根大柱子一旁的柜台说:
晓球得那个瓜娃子是不是去开啥子朗诵会去了!
没找到胡涂,但找到了他上班的地方,这让人喜忧参半。胡涂开的诗歌朗诵会,无疑就是我要去开的那个会,让人喜出望外。然而,找不到胡涂,我过夜就成问题,天快黑时,东问西问找到了考古学家的家。开门的是一个姑娘,人背着屋里的灯光,还没看清她的长相,考古学家就从姑娘后面钻出来。他见到我并不惊讶,听我说完来意后,径直把我带到平房后面的牲口棚里。那是一个挺不错的棚子,当中吊着一只灯泡,两匹马正低头吃着木槽里的东西,其中一匹是后腿老长前腿太短的怪马,
你参加工作了吧?考古学家说。
我在当知青。我说。
我大女儿也在当知青,就是刚才给你开门的那个。他说。
我没看清楚,说不定我认得。我说。
这么晚了,吃晚饭没有?他说。
吃过了。我扯谎说。
要是没吃,可以跟马一起吃,槽子里的东西挺不少,马吃不完。他说。
我真吃了。我说。
对了,你就睡这里。他指着棚子的一角说。我扭头一看,那里有张单人床,看上去睡觉的东西样样不少。
我家里太挤,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家,住不下。他解释说。
跟马睡一起,没关系。我说。
我平常也睡在这个地方。他又说,好像担心我会怪罪他。
只要明天早点叫我起床就行。我说。
肯定没问题,我今天夜里就是不睡觉也会叫醒你。他大声说。
你不睡觉咋行?我说。
你来了,我就没地方睡了。他说,大步出了门。
考古学家说他刚才开门的女儿也是知青,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从前来我家说起过的那个女儿,就是那个几岁大跑跑城边上去看修铁路的女儿。不过他的两匹马,我认识其中的一匹,那畜牲要比我这个从农村跑进城来开诗歌朗诵会的知青有来头得多。夜里,我被饿醒,爬起来到马槽里抓了些东西大嚼一顿。灯光有些暗,马槽里是些什么食物看不大清楚,不过味道还行,美中不足是稍有些割舌头,扎嗓子。
第二天早晨,第一个赶到县文化馆会场的可能是胡涂而不是我。
一进大门,我就撞见他从会场里出来,一眼认出了他。几年不见,他长高了一个脑袋,但仍旧是从前那种长相。擦身而过时,我忍不住刚要叫一声胡涂,他却昂头棱了我一眼,同时愣了一下,接着一声不吭走过去,好像没认出我来。见他那种样子,我有些拿不准下一步该不该先跟他说话,也拿不准到时候好不好跟他说去商场找过他。馆长来了,我把一首四句短诗交给他,接着奉命扫地,搞了一屋子灰尘,没看清另外一个来回搬桌椅又擦又洗的是不是胡涂。当时,天刚麻麻亮,大约七点钟光景,也可能六点左右,反正提前到会场干活的就我跟胡涂两人。等后来人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陆续到齐了,我又奉命在会场和附近的一个茶馆之间忙着提开水。馆长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当众把他嘴上的一个过滤嘴烟屁股取下来塞在我嘴里,那一刻,不少人眼瞪着我抽他们从没见过的过滤嘴香烟,羡慕得很。
上午九点,会场坐满了文学工作者。胡涂已经停下手里的活,正独自一人坐在会场门口外的一堆砖头上,歪斜脖子望着会场,一副翘首以待的神情。诗歌朗颂会即将开始,满面春风的馆长开始介绍与会者:
这位是我们县上老资格的文学工作者、土地大队六圃子的会计黄有财同志!
会场中站起一位乡绅模样的老者,掌声响了起来。
这位是很多产的……
麦克风突然一阵尖叫,旋即不再叫,站起来一位蔬菜公司的会计,又是一阵热烈掌声。介绍和鼓掌花去不少时间,惟独没介绍我,显然也没介绍门口的胡涂。但我觉得,单凭一个过滤嘴烟头和馆长给的那一张通知,就表明人家没把我当一般人。于是,我提着开水瓶给每一位沏茶,又给门口的胡涂端去了一杯茶,他头也不抬,显得不屑于抬头。后来再去给他冲开水时,才发现他走了,茶杯里的水被喝得没留一滴,只剩下干茶叶。我当即想到,仅凭这一点,我就一定会跟他合得来。
直到朗诵会开完,我也没能上台朗诵我那四句诗。下午,农场的马车真来接我了,赶回农场已近黄昏。走进大房子,一眼就看见窗前我的箱子上赫然摆着一封信,信封后面的邮票上盖了邮戳,拆开一看是校花写来的,急忙藏进兜里。大奶和孔都不在,我独自来到山坡上,再一次打开信细看,不由瞪大了眼睛。校花在信中一句好话没讲,先说我们都是改天换地的闯将,接着笔锋一转,把自己说得更坏,批判得更厉害,保证得更加铿锵有力,简直比我更像一个马上要去赴汤蹈火将功补过的亡命徒。而且,她不但横眉冷对自己,还顺带着批判起我来,那股风卷残云的劲头,差一点就把她自己和我都比成了历史反革命。我战战兢兢地想,我去信只说了自己怎么坏,没说她半句坏话,而她回信把我也给搭上,太不留情了。
农场无信箱,校花的回信不知是农场何人从公社取回来的。接下来的每一天,我都要偷偷看一眼那封信,越看越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后来信纸都看烂了,也没看出校花真正想说些啥。最后琢磨出,她的真实意思可能是说既然咱们都这么坏,那就在农村老老实实脱胎换骨,别的什么事都是痴心妄想。
这种猜测把我打击得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然而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一生中第一个通信的女人,尤其是我们双方都明白自己太坏,看样子根本就没把我当外人,表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使我即感到满足又觉得可怕。本想又去信抛砖引玉让她再狠批一通,但日子太苦太累,我很快就没心思再想她,从此以后相互间也再没有任何书信来往。我估计她痛痛快快批判一通后也早把我忘了,不然不会没再写来一个字。后来每逢赶场天,我和她多次在公社旁边那条挤满人的破烂老街上相遇,照样没说过半句话,完全就像从不相识,谁也没干过什么勾当一样。
但我依然忘不了校花给我缝过裤扣,还有小时候在京剧团扯过我鸡鸡,还有在马道路上亲手遮过我裤裆,还有还有很多。有一次在拌桶前脱谷粒,我又想起她,一大把谷粒突然飞进眼睛,疼得我抱头鼠窜,满稻田翻滚。几个知青按住我,农场那个每天跟大家一起出工的女卫生员几步跑来,在把谷粒一颗一颗弄出来时,差点把我的眼珠给抠出来,她的无名指也险些被我一口咬断。我的两眼出血不止,一片尖叫混乱之中,大奶和孔照场长吩咐把我送回农场,又帮我打饭打洗脸水,然后陪着我走几小时山路,送我上了回马道的火车。
第十四章 火车上的遭遇
第十四章 火车上的遭遇
铁路医院的住院部大病房里,十多张病床都空着,只有我一个病人。医生把我两眼都用纱布蒙住,使我看不见守在身边的我爸和我妈,也无法出病房去外面看一看那场军列救援留下的场景。晚上,几个弟弟和二哥来了,没呆一会又先后离去。要是大哥能来看我,一定能从火车司机的专业角度,跟我说说那趟军列失控与救援又是怎么一回事。但大哥在跑车,平时也难回一趟家,我靠在病床上,只能听我爸以外行人的眼光来讲。等他兴冲冲地一口气讲述完亲眼所见的整个救援行动,我妈接着又用不无遗憾的口吻让我明白,那条新铺的救援紧急避难线早已拆掉,现场已被连绵夏雨抹掉,还长出了绿草,要是我早些天回来,兴许还能见上一见留下的痕迹。
我眼前一片黑暗,又听见我妈向我打听,老包的儿子大奶回农场后怎么样了?我爸立即插话数落我妈,说她不先问问自己的儿子在农村干得怎样,开口倒先问人家的孩子。我担心两人吵嘴,接我妈的话回答说老包的儿子挺好的,除了干活累,别的没啥。不料我妈说,老包住院那些天,老古的那个老婆每天下班都来守护,到后来还几次扶老包进男厕所,有一次被老包的爱人看见,气得不得了。
老包的儿子不是一直在医院陪着吗,怎么还用得着老古的老婆?我说。
那孩子一个大活人,哪能没日没夜老守着呢?总得回一回家,看看他妈妈吧。我妈说。
老包的爱人没来守?我说。
来过几次,但老戴个大口罩,就被老包劝回地陷湖家里去了。我妈说。
你和我爸不是也来帮着看护了吗,也用得着老古的老婆?我说。
我和你爸爸是常来,连你师傅都守护过,但总得上班,家里也得有人做饭呀。我妈说。
我妈说话的语气听着挺不对劲,好像老古的老婆跟老包有问题了。我记得几年前,我师傅背老古的老婆来住院那次,出院时就是老包派小汽车把她接回家的。她可能是为了感谢老包,才来看护老包的。但我一说出这层意思来,我妈马上就反对。
要那样就好了,可我发现就不是那么回事。她说。
别背后议论老包。你忘了咱家在成都倒霉那些年,老包从没斜眼看过咱们家。我爸忽然又制止我妈说。
是啊,我也没胡说啥。我妈马上变了说法。
我爸的话声听起来,还是我小时候在成都听惯的那种腔调。虽然看不见他,但我能看见他在成都被红卫兵们追着往死里打的情形,好像还能听见他每天夜里发出的那些可怕的梦话。沉静了片刻,我对我爸我妈冷冷地说,我要跟他俩说一件事,说一个人。
说,啥事?我妈说。
是不是见到那个小丫头啦?我爸说,指的是校花。
少提她,提她我就烦。我说。
咋突然变成了这腔调,是不是你在农村给家里惹啥事啦?我爸说,口气一下担心起来。
我说没惹事,也没出事。接着,一句一顿地说出了我爸的,同时也是我妈的,同样更是我们全家的仇人:雷巴。
雷巴两个字,使我爸我妈一下全没了声音。等我接着把雷巴以及他伙知青跟我之间的事,包括雷巴跟校花怎么好、校花的哥哥怎么被人提刀追着跑,一点一点全说出来以后,我爸又静了好一阵才对我说:
你没找你师傅,跟他说说?
找他干吗?我说。
跟他说说雷巴在成都怎么整的我,看他怎么说。他是你们公社知青带队干部,毕竟是你的师傅,在成都还放跑了我钓的那条大鱼,没准会帮忙。我爸说。
咱家的事还去求人家,就我自己也能收拾雷巴!我说。
不行!雷巴那小子打武斗时啥都敢干,就算你和师傅俩人加在一块,也不见得就是他的对手。得了,你要向你大哥学习,千万别再去招惹那家伙。
哼,你就忘了雷巴怎么收拾的你!我妈说,不满我爸。
我爸叫我别听我妈说的,要我像大哥那样在农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然表现差了别想招工。又说校花那个丫头,她爱跟雷巴怎么好,少去管。还说她哥哥在成都就不是好东西,被人拿刀追着逃命,活该!
接下来的每一天,我爸都来催问我的眼睛好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