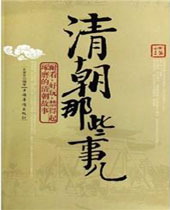成都--那些走远的人-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二十章 成都各大造反派被命令缴枪
连续几天,远近枪声不断,时起时伏。
武斗一暂停,老古就来我家看对面吴清华回来没有。等他失望一离去,我妈就说老古还在惦记着看女娃子屁股。但老古关心的可能早已不只是吴清华洗澡时亮出来的屁股和奶奶,他在外面说,雷巴已被抓到郊外跟另一些不知哪一派被俘的人关在一起,一律脱光上身,被一根长粗铁丝穿过肩夹骨连成一排,像一串糖葫芦。又说雷巴一被抓,双方第二天半夜对打起来,雷巴他们八二六强攻野鸭子,投入了空前火力。多次强行营救,有一次差点救出雷巴来。野鸭子边反击边用大喇叭喊话,说他们死了一个副总司令,要八二六造反派必须交一个总司令,至少副总司令去抵命,否则绝不放人。
老古说的这些话一传到家里,我妈就在饭桌上问大哥:
雷巴不是铁中造反派的头头吗?
一提雷巴,我爸忙起身去关好窗户,又检查门关好没有,然后才坐回桌边。大哥说:
我早就打听过,铁中先前有好几个造反派组织,后来毛主席说要大联合,就合为一个大造反派,雷巴只是一个分派的头头,总司令部里面的正副司令是其他人。
我爸认真听完每句话,接着问大哥:
以前不是跟你讲过,雷巴说的那个老歪,查没查出来到底是谁?
大哥说,我暗中打听过,好像是有这么个人,说是总司令,但不怎么抛头露面,不知道是不是红卫兵假设了这么个总司令,好让别的造反派看不见找不着,就更能震住对方。反正打听来打听去,人家一般都不爱跟我们这种类人说真话。
二哥说,我早就派了好几个弟兄去查过,也没查出来。
我爸说,就你,还能派人?
二哥说,是啊,能啊。
我妈说,派的是啥人哪?会不是街上的叫花子吧?
二哥说,哪能呢,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满地打滚的那些人呀。
说完这些事,我爸才叫我又去打开窗户。对面窗户依然每天关着,白天看不见吴清华,但不知会不会天黑后她才进进出出。趁枪声停歇,我下楼去玩,孔又坐在窗下玩鸡鸡。他跟我说,铁中里面有一大堆武斗打烂的汽车,弄一些铜管可以卖钱。我问他是不是那个交通员透露的。他点点头,说是吴清华那个小弟弟去铁中找他姐的时候看见的。
铁中早就封住了大铁门,我来到静悄悄的校园背后,想翻墙进去。沿着围墙有一条两米宽的水沟,只有一处挺窄,沟边的荒草已被人踩倒。我从那里过了沟,在墙下跳起来手一抓墙顶,但最高处的几块砖一松动,差点砸下来。我一下撒手跳下来,退到河沟那边,望着墙顶不敢再翻墙,接着转身快跑着离去,生怕被人看见。夜里躺在床上,那几块砖老在眼前晃动,谁要是再去那里翻墙,多半要被砸破脑袋,难说会不会砸出人命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梦里猛听见我爸在楼下跟人大声吵闹,忙下床爬到窗口,看见他跟校花的哥哥正站在楼外面,两人已停止吵闹。很久没见到小校花的哥哥了,我一时还以为仍在做梦。等小校花的哥哥看着我爸小声说话时,我才明白是真的。我爸听对方说着什么,一副哑口无言的模样。他听着听着,手上的铝饭盒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最后,小小花的哥哥朝远处走去,看样子回家去了,我爸抬头看了一眼二楼家里的窗户,一眼看见了我。然后,他拾起地上的空饭盒,进了门洞。
看情形,我爸是下了夜班回家,刚走到楼下被小校花的哥大哥拦住的。他从大声吵闹变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瞬间的事,我永远忘不了他抬头看窗户的那张惨白的脸。一会,他走进家门,显得闷闷不语,心事重重,我妈问他什么话,他都带答不理,恍里糊稀像没听见一样。我不敢跟他说话,也怕他突然问我话。小校花的哥哥是铁中的学生,我怀疑自己爬围墙弄坏几块砖的事被他发现,专门找我爸告状来了。我还想,我爸跟他那个户籍民警爸爸闹翻,早已是公开的事,户籍民警丢枪挨批斗时,我爸又指使二哥把他踢倒在台上,他那个当儿子的不会不知道。因此,来找麻烦了。
以后的每一天,我一次次走近那里,看那几块砖还在不在墙顶上,心里盼着有人已把砖头爬掉,但那几块砖头仍旧歪斜在原处,我的心就一直悬在墙顶上,唯恐哪一天出人命案。我相信一旦那样,我定会被抓起来,公安也一定能抓住我。说不定来抓我的就是户籍民警。我甚至想好了到时候怎么撒谎、狡辩,如果要坦白,话又该怎么说。
无处可玩,我到外面去找铁丝,不是粗的,而是细的那种。铁中背后的农民菜地竹架上就有,但我已不怎么再敢去,只能去了几次西北桥和人民北路两个菜市场。那两处菜市,也是我们那一带家家户户平时买油盐酱醋的地方,但只有一些发霉的稻草顶的店铺,有些墙面就是掉了外面糊的泥块,也只能见到露出来的竹笆墙,而没有铁丝。我要是找得到细一些的铁丝,就能用我爸那把钳子做手枪式的弹枪,能一只手握着连发五颗纸做的子弹。
在成都,不容易找到细铁丝,但我在外面捡到了一些硬纸片和一大叠花纸。于是,用一只笔加上煮饭的稠米汤,没完没了地做起扑克牌来,每跟大奶几天玩烂一副就接着又做。直到有一天用完了花纸,我就跟大奶一起用几颗钉子几块破木板做一个模具,然后装进筛好的细河沙,再用借来的皮带扣印好模型,把捡来的牙膏皮放在蜂窝煤火上熔化,一会工夫就浇铸成一个皮带扣。成形后的皮带扣用砂纸打磨光亮,再剪掉书包凡布背带,费不了多少事就制成了红卫兵那种很神气的腰带。
我和大奶就是捆着那样的腰带,在楼外那片很久不种庄稼的农田里放了起风筝来。
风筝由我们自己动手做,只需要作业本纸、竹片、稠米汤就行,当然要把握好结构比例,不然风筝一起飞就往下栽。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没钱买风筝线,偷我妈缝衣服的线接长用,也不太结实。有风的时候,我们在田里跑来跑去,手拽着线不停往后退,好让风筝启动上天。田里有个大粪池,一间屋子那么大,粪水和漂浮的一层腐烂菜叶几乎与池边一般平,我们特别留心。但有一天,吴清华的小弟弟也出来放风筝,往后退时一下掉了进去,我们急忙大声喊叫救命。
就因为那一阵拼命喊叫,我和大奶肚子一用力,腰带扣一下断裂开,裤子跨了下来。
我们顾不了裤子,一直喊叫,但吴清华的小弟弟沉下去又浮起来,两只手在外面摆动几下又搭拉下去,最后只剩下后脑勺露在面上,头发差不多和粪池面上的东西一种颜色。
等他被跑来的大人捞起来摆在坑边之后,我才看见两个姑娘和一个老妈子跑来哭着扑上前去,只是没见到吴清华。孔的交通员死了,他一副难过的样子。他在一片哭声中小声对我和大奶说,那两个姑娘,跟我们一般大的那个是吴清华的小妹妹,半大的那个是大妹妹。也就是小弟弟摸到了她下面那个稀不拉几的地方。
要不是我和大奶都各自手提着裤子,我们定会前去看一看姐妹俩,至少我会。
远处枪声变得零星稀落的时候,从四面把方传来了抢劫集团的各种传闻。说是有一伙造反派,每天夜里开着大卡车进家属区砸门入户抢东西,已有不少地方遭殃。居委会当即立断,组织每家各出一人,每天傍晚关闭堵死门洞大门,天一黑就爬上楼顶持枪轮流站岗放哨,一旦出现可疑迹象立即鸣枪。一听见枪声信号,家家户户不能开灯,要马上敲响准备好的铝盆、锅盖等东西,附近的各大红卫兵造反派一听见动静,就会火速赶来武装增援。
几个夜晚安然过去,但在我妈和邻居老包值班的那天下半夜,老包鸣枪了。整栋楼里很快响起各种敲击声,不远处的大片居民区也跟着响成一片。紧着着,附近几个方向响起了阵阵枪声和高音喇叭声,发出的男女喊声低沉而悠扬,荡过茫茫夜空:
同胞们,八二六来了!我们来了!
同志们,坚持住,我们反到底来了!
现在警告抢劫集团,你们放下武器!必须立即向野战部队投降!
一喊完话,随即响起几种雄壮的战斗进行曲,响过一阵又重复喊话。我们都听见了高音喇叭,我还听出红卫兵造反派是如此强大,恐怕除了造反派,没人敢动一动他们当中的雷巴那些人。我敲打着一个破铁桶,摸黑满楼找我妈。楼上楼下到处是看不见的人,最后找到我妈时,她正用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向居委会报告,说是她在楼顶上一眼发现抢劫集团来了!是先发现几辆卡车在老远的马路边停下,过一阵才从车上跳下来许多人影。
当夜无事,之后的几天也一样,但后来有一天不同了。
那天夜里,楼外悄静无声,楼里的人们走家串户议论纷纷,都被反常的宁静弄得忧心忡忡。我爸跟老包下了两个回合象棋,我跟大奶在一边观战,发现老包心神不定,每动一子都要考虑半天,但一出招就明摆着是臭棋。我爸无心再战,提议休息,叫老包到家里坐一会。那不过是随口说的客气话,老包却真进了我家,人一坐下,神色变得更加慌乱。
我爸说,你就别再疑神疑鬼啦。
老包说,你老弟不知道,我前一阵从外面回来的时候,铁路全线停了工不说,而且我们山里的工地上也打武斗了。
我爸说,全国哪儿都一样。
老包说,你老弟不知道,我们那些打武斗的人先是用打隧道的钢钎、大锤、风枪什么的对攻,接着把推土机改装成坦克,把挖掘机变成装甲车,把开洞放炮用炸药、雷管改成土炮弹,很多东西都派上了用场,工地上的施工设备全给毁了。
我爸说,死人啦?
老包说,成万成万的施工人员全跑了。跑的时候,一节又一节经过改装的平板车上坐满了人。平板车沿着铺了轨的铁道线顺着大坡往下溜,车上没刹车装置,也没有喇叭,那些人就在车上,边溜边敲锣,遇上转弯就用一根根准备好的木棒插下去,刮着枕木减速。我就是这个样子跑回来的。
我爸说,可了不得!人回来了就别再老想啦。
老包说,你老弟不知道,那条成昆铁路,我参加过几次勘测设计,后来又参加修建,心里堵得慌啊。
几声叹息之后,老包缓缓说起从前他带着队伍勘测和修筑成昆铁路的事。
夜里,外面一直很静。我们正在听老包讲山里一条铁路的往事,窗外斜对面的马路那边,突然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声,火光顿时照红夜空。我们顿时全都爬到地上,躲到玻璃震碎的窗户边,发现31中的教学大楼大火熊熊,少了半边。
后来,连消息灵通的老古也说不清炸楼是怎么回事,只听说那天夜里雷巴活着逃了回来。
不久的一天晚上,对面窗户终于打开了,屋里站着雷巴和吴清华。我爸正好当夜班,总在外面逛的老古又钻进了我家。跟以前一样,他先叫我关了灯,然后站到窗口看着对面。虽然对面两人又搂在了床上,但窗前那盏大灯泡仍照得这边什么也看不清。而且,天气已无比寒冷,等雷巴离去后,吴清华也并没像从前那样一丝不挂地站在屋当中洗澡。
转眼已到春节,难得再听见武斗枪声。但不管什么地方都难再买到新鲜猪肉,连外地运来的冻肉冻带鱼,人们也见了就抢。年三十凌晨一点,我出去找了十几个地方,最后在一个十里外的肉铺前面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