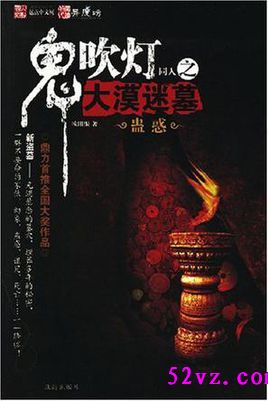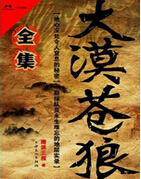大漠谣II-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日磾已经认出你了?”
“他很谨慎,只看了我一会就走开了。”
霍去病揽我靠在他肩头,“就冲他这份对你的爱护之心,我也该请他喝一次酒。“
他忽地看到我裙上的血迹,脸色一变,立即将我一直拳在袖子中的另一只手拽了出来,“你……这是……”他的声音都卡在了喉咙里。
我笑了笑,想要解释,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其实有借口也瞒不过他,遂只是望着他笑,示意他不必介怀。霍去病默默看着我,眼中都是痛楚和自责,手指轻轻抚过我的笑容,一低头吻在了我的掌上,唇沿着伤口轻轻地,一遍遍地滑过。
去病,有你如此待我,我不委屈。
――――――――――――――――
“玉儿,有位夫人要见你。”红姑神色透着紧张,惹得我也不敢轻视,“谁?”红姑道:“是……是陈夫人。”
我愣了一瞬,明白过来。这两日一直呆在霍府,没有回过园子,今日刚进门,卫少儿就登门造访,看来她对我行踪很清楚,也刻意不想让霍去病知道。
我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自己,侧头对红姑说:“请陈夫人来这里吧!外面人多口杂不好说话。”
红姑却没有立即走,看了我一会,方道:“小玉,宫里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一二,霍将军为什么不肯接受皇上赐给他的府邸,还说什么‘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们听了,虽然很是景仰他的志气,可匈奴哪里能那么快杀光?难道只要匈奴存在一日,他就不娶妻生子吗?卫青大将军已经有三个儿子,妻子都已经换过两位,还有一位是公主,可也没见卫青大将军就不能上沙场打匈奴了。”
我还没有回答她的话,就看见心砚满脸委屈地带着一个中年美妇走进院子。中年美妇微含着一丝笑,看向我,“你就是金玉吧?红姑迟迟未出来,我怕你不肯见我,就自做主张了。”
我忙上前,恭敬地行了一礼,“怠慢您了,本就想请您到这边说话,比较清静。”红姑和心砚都向卫少儿行了一礼后,静静退出。
卫少儿随意打量了我的屋子一圈,敛去了笑意,“我不想拐弯抹角就直话直说了。若有什么让姑娘不舒服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我微微笑着点点头,一个人的份量足够重时,自然令他人说话时存了敬重和小心,在这长安城中,我不过一介孤女,不包涵也得包涵,不如做到面上大方。
“公孙敖曾对我说,你行事不知轻重,一个狐媚子而已,去病在军中行事不检点,你不但不劝,反倒笑看,我听了心中也很不舒服,虽然没有指望去病娶一个多么贤德的女子,可至少要知道行事谨慎,懂得进退,朝中对去病多有骂声,我一个做母亲的听了很难受。我问过皇后娘娘的意思,出我意料,娘娘竟然很是偏帮你,一再叮嘱我们不许为难你。能让妹妹看上的人,应该不尽是公孙敖所想的那样。所以今日我来,只是作为一个母亲,想心平气和地和你说几句。”卫少儿一面说话,一面查看着我的神情。
我欠身行了一礼,“夫人请讲,金玉洗耳恭听。”
她面上忽闪过几丝黯然,“去病的身世,你应该都知道。既然当年我做了,我也不怕提,我未嫁人就生下了他,他出生未久,他父亲就娶了别人。去病在公主府,半跟在他舅父身边长大。其实去病心中一直很想要一个正常的家,可你如今让他……”她苦笑着摇摇头,“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已经不是孝顺不孝顺的事情,长安城中二十岁的男子有几个还膝下犹空?金玉,我今日来,只是作为去病的母亲,请你再仔细考虑一下。如果……”她盯着我道:“如果你能离开去病,我感激不尽。”
我沉默地盯着地面,如果是别人,我可以不管对方说什么都置之不理。可这个女子是去病的母亲,没有她就没有去病,是他的母亲在这里殷殷请求我的离去,心一寸寸地抽痛,可面上更不敢丝毫泄漏。
卫少儿等了半晌,看我依旧只是垂头立着,“金玉,我也曾年少轻狂过,不是不懂你们,可是人总是要学会向现实低头……”
门“咣当”一声被大力推开,霍去病大步冲进院子,眼光在我和卫少儿脸上扫了一圈,俯身给母亲行礼问安,“母亲怎么在这里?”
卫少儿看向我,眼中几分厌恶,“我从没有见过金玉,所以来看看她。”
霍去病道:“母亲想要见玉儿,和我说一声就行,我自会带着玉儿去拜见母亲。”
卫少儿讪讪地,一时没有妥帖的言词,我忙笑着反问:“夫人正和我说长安城新近流行的发髻,难道你也想一块探讨一下?”霍去病探究地看看我,又看看卫少儿,卫少儿点了下头,“我们女子总有些私房话说,出来得久了,我要回去了。”
霍去病随在卫少儿身侧向外行去,侧头对我道:“我先送母亲回府。”
虽已是冬天,阳光仍旧明丽,泼泼洒洒地落满庭院,可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心只阵阵发凉。
“玉儿,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脸色这么苍白?”红姑扶着我问,我摇摇头,“你派人通知的去病?”
红姑轻叹口气,“陈夫人这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园子中,真有什么事情,你为了霍将军也肯定只能受着,我怕你吃亏,所以她一进园子,就暗地派人去霍府了。”
我强笑道:“陈夫人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我能吃什么亏?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再惊动去病了,我自己能应付。”卫少儿误以为是我拖延着不见她,暗中却通知了霍去病,对我的厌恶又深了几分。
红姑迟疑了一瞬,无奈地点点头。
红姑扶我进屋后,倒了杯热茶递给我,“玉儿,你知道吗?石舫分家了。”
我顾不上喝茶,立即问:“怎么回事?”
红姑道:“这段日子长安城内的商人估计人人嘴里都这么念叨,几日间,长安城内最有势力的石舫就分崩离析。你不知道因为石舫,长安城内的玉石一夜之间价钱就翻了两倍,因为人人都怕陈雨经营不好。药材也是一直在涨,但陆风身边因为有石舫以前的三大掌柜之一石天照,在石天照的全力周旋下,才勉强压制住药材价格的升幅。如今看风、雨、雷、电四人行事的样子,的确是有怨,争起生意都不彼此客气,互相也再不照应对方。外面传闻是因为九爷身体不好,再难独力支撑石舫,而底下人又各怀鬼胎导致。玉儿,你看我们是否应该找个机会去看看九爷?”
我心内如火一般的煎熬,他竟然说到做到,真地要放下一切,放弃家族多年的经营。突然想到这个分配有遗漏,急问道:“那石大哥和石二哥呢?怎么没有他们的生意?”
红姑摇摇头,“不知道,听闻好象是争钱财分配时,他们内部出了矛盾,石谨言是个缺心眼的人,被其余几人算计了,负气下离开了长安城,石慎行和他如亲兄弟一般,伤心失望下也举家迁徙离开了长安。”
石大哥和石二哥都举家离开了长安城,看样子是不会再返来,他们能到哪里去?红姑问:“我们卖吗?”
我愣了一会,缓缓道:“就卖给章电吧!歌舞坊的姑娘跟着他,我还比较放心一些。”
红姑点点头,颇有些留念地环顾着四周,忽地道:“我从很小就住在这里了,我想把我们自己住的这个后园子留下,只把前面的园子卖给章电,砌两道围墙隔开就可以了。”
我想了想,“可以,前面的屋宇已经足够,价钱要低一些,章电应该也不会反对,我也在这里住习惯了,一日不离开长安倒也懒得再动。”
红姑笑接道:“难道嫁人了,你也还赖在这里?”话一出口,她立即惊觉,担心抱歉地叫道:“玉儿……”
我摇了下头,“没事,我不是那么敏感脆弱的人。”
红姑默默出了会子神,叹道:“以前总盼着你捡一个高枝去栖,所以看出霍将军对你有意思,而你对他却不冷不热,就一直盼着你有一天能动了心,可以嫁给霍将军,可现在……我突然觉得你跟着他是吃苦,这个高枝太窄、太高,风又冷又急,四周还有猛禽,你若能嫁一个平常点的人,两个人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其实比现在强。”
我握住红姑的手,“有你这样一个姐姐,时刻为我操心,我已经比园子里的大多姑娘都幸福了。我没有那么娇弱,风大风冷对我算不了什么。”
红姑笑拍拍我的手,“自你离去,石舫对落玉坊诸多照顾,此次的事情外面传得纷纷扰扰,你要去看看吗?帮我也给九爷请个安。”
我撇过头,轻声道:“这事我会处理的,姐姐就放心吧!”
―――――――――――――――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细细碎碎并不大,时断时续,却没完没了,连着下了四天,屋顶树梢都积了一层不厚不薄的雪。地上的雪部分消融,合着新下的雪,慢慢结成一层冰,常有路人一个不小心就跌倒在地。
“玉姐姐,你究竟去是不去?”以前的石风,如今的陆风瞪着我嚷道。
我轻声道:“你怎么还这么毛躁的样子?真不知道你怎么经营生意。”
陆风冷笑一声,“我做生意时自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是我姐姐,我才如此,不过我看你现在一心想做霍夫人,估计也看不上我这个弟弟。反正我爷爷想见你,你若自己实在不想动,我也只能回去和爷爷说,让他亲自来见你了,只是不知道你肯不肯见他,你给个交待,我也好向爷爷说清楚,免得他白跑一趟。”
我望着窗外依旧簌簌而落的雪,沉默了半晌后,缓缓道:“你先回去吧!我随后就去石府。”
想着老人图热闹,爱喜气,特意拣了件红色衣裙,让自己看着精神一些。马车压在路上,冰块碎裂的喀嚓音,声声不绝地传入耳中。这条路我究竟走过多少次?有过欢欣愉悦,有过隐隐期待,也有过伤心绝望,却第一次如今天这般煎熬痛苦。
除了小风还住在石府,其他人都已经搬出,本就清静的石府,越发显得寂寥。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萧索。
我撑着把红伞,穿着条红色衣裙,走在雪中,好笑地想到自己可是够扎眼,白茫茫天地间的一点红。
过了前厅,刚到湖边,眼前突然一亮,沿湖一边一大片苍翠,在白雪衬托下越发绿得活泼可喜。石舫何时在湖边新种了植物?不禁多看了两眼,心头一痛,刹那间眼睛中浮了水气,看不清前方。
似乎很久前,仿若前生的事情。一个人告诉我金银花的别名叫忍冬,因为它冬天也是翠绿,他不肯说出另一个名字,也没有答应陪我赏花。现在这湖边的鸳鸯藤,又是谁为谁种?
世界静寂到无声,雪花落在伞面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我在鸳鸯藤前默默站立着。当年心事,早已成空。泪一滴滴打落在鸳鸯藤的叶子上,叶子一起一俯间,水珠又在积雪上砸出一个个小洞。很久后,叶子再不颤动,我抬头对着前方勉力一笑,保持着自己的笑容,转身向桥边走去。
一个人戴着宽沿青箬笠,穿着燕子绿蓑衣,正坐在冰面上钓鱼。雪花飘飘扬扬,视线本就模糊,他又如此穿戴,面目身形都看不清楚,估摸着应该是天照,遂没有走桥,撑着红伞,直接从湖面上过去。冰面很是光滑,我走得小心翼翼,不长一段路,却走了好一会。
湖上凿了一个水桶口般大小的窟窿,钓杆放在架子上,垂钓人双手拢在蓑衣中,旁边还摆着一壶酒,很闲适惬意的样子,“石三哥,小雪漫漫,寒湖独钓,好雅性呢!”
他闻声抬头向我看来,我的笑容立僵,站在当地,前也不是,退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