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logy思维空洞-第1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章悦忽然摇了摇头,她俯下身子,将万储扔在地上的裤子捡起来,将上面的皮带唰地一下抽了出来。
猛然间,她轻斥一声,扬起皮带,抽在了万储的身上。
“啪!”地一声响。
万储的腰间多了一条红色的长条。
他痛叫一声,愣在了原地。
章悦在笑,笑得不怀好意。
万储忽然大吼一声,将章悦大力推倒在控制台上,一把夺过皮鞭,猛地朝着章悦身上抽去。
“啪!”一声脆响!
章悦大叫一声,躺在了控制台上,雪白的身上随即出现了一条红色的印记。
万储二话不说,又是一鞭子挥下,随后抬脚跨上了控制台。
“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万储的话还没有说话,章悦忽然抬起手,“啪!”的一声,打在了万储的腮帮上。
万储感觉又愤怒又羞耻,但是隐隐约约,他好像还感觉到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激动。
他尖叫一声,同样一巴掌打在了章悦的脸上。
随后,伴随着章悦一声呻吟,他长驱直入,完成了第一轮的冲杀。
就在这时,章悦斜眼瞥到了身侧的电脑屏幕上,她的一只手伸出,偷偷按了几下键盘,另外一只手在鼠标上快速按了两下。
不知是意外,还是章悦的有意为之——
电脑竟然切换到了麦克风语音对讲模式。
102,103,还有201,全部都进入了语音对讲模式。
伴随的万储的动作,章悦在剧烈地喘息。
她呻吟着,浪叫着,声音此起彼伏。
她的叫声通过电脑旁边的一个麦克风传进了那几个病房里面。
这是一场声音的活春宫。
让人的想象力奔驰到极限。
102病房内是十二生肖,他在第一时间听见了这个声音,三秒钟之后,他就从地上站了起来,随后,他全身扑倒在地,双手合十放在脑前,双脚合并在身后,他的身子成了一条直线,但是很快,他就在地上蠕动了起来。
他一边蠕动着,一边抬起了头,舌头自口中吐出,一伸一缩。
他的模样像是一条蛇……
果然,他再次切换了自己的动物形态。
与此同时,103病房的铁胃金刚牙也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的肚子一起一伏,只不过起伏的幅度越来越大,他的眼睛也睁得越来越大,随后,他缓缓张开嘴巴,露出了一双血红色的牙齿。
他的牙齿似乎本身就是红色的!
他呲着牙,从床上站了起来,走到监视器的墙壁前,抬起头,面对着镜头。
他的牙上在往下滴血,滴进嘴巴里,迅速被他吞咽。
同时,201病房,鬼手魔山的病房,也传进去了章悦的叫声。
在这间病房的床上没有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似乎住在这里的病人从来都没有睡过觉。
在电脑屏幕的第二个镜头上,终于看见了鬼手魔山的影子。
此时,他正笔挺地站在右边的墙壁前,面部紧贴着墙面,似乎正在面壁思过。
他的身高果然很高,他的头距离天花板也就只有半米的距离。
他的体形果然很庞大,整面墙壁在他的身躯面前都似乎显得有些弱小。
他上半身赤裸,皮肤古铜色,身上的肌肉块块凸起,连成一串,如同盘根错节的钢筋一般。
他像是一块巨石,坚硬强悍。
他像是一座山丘,坚固沉稳。
听着章悦从麦克风中传来的声音,他依旧一动不动地面对着墙壁。
在这面墙壁的另外一边,便是202病房,也就是催眠大师梁哲所在的病房。
难道,他已经知道催眠大师梁哲再次回来了?
但是,这面墙是钢筋水泥外加精钢熔炼凝结而成,厚度足足有一米半,纵然是500分贝的声音也无法穿过墙壁,他怎么可能知道梁哲回来了。
但是,面对章悦突如其来的叫声,他竟然纹丝未动,这多少有些奇怪。
忽然间,他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章悦的叫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力,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他倒退着往后走了几步。
随后,他猛地往前冲去。
“咣!”地一声巨响。
他的头撞在了墙壁上。
墙壁微微震颤。
鬼手魔山站在原地,双手按住墙壁。
随后,他缓缓转过了头,望向了监控器。
他房间内的监控器是特殊制造的,被嵌进了钢筋铁网里面,就是为了不被他轻而易举地毁掉。
他的眼睛出奇地大,足足有小孩子的拳头那么大,里面闪烁着愤怒的火焰。
似乎,不管任何时候,他都是愤怒的!
就在这时,章悦扭过头去,透过监视器,看见了鬼手魔山的真面目。
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随后,她高声尖叫,高潮来临。
她甚至不知道这是因为万储,还是因为屏幕里的鬼手魔山——
她看着鬼手魔山的身躯,双眼再也移不开分毫!
他那巨大的身躯,如同一座山,压在了她的心头。
她知道,自己又有新的高山要去征服了!
第231章 铃儿去哪了
病人逆反战斗开始前一天的晚上,铃儿在自己的房间内哭成了泪人。
小玉被院警诬陷成了两起凶杀案的凶手,现场找到了她戴的黄色手环,那成为了定罪的证据。
院警们直接在会议室内对小玉进行了粗暴的审判。
最后,在院警们的淫威之下,小玉屈打成招,成为了罪人,被关进了地下室,隔日即会进行处决,用她的性命祭奠两名死者的灵魂。
弱小的铃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强行关押,然后被处死。
她无能为力,她没什么本事,也没有人缘,更没有权利,她说的话别人权当是放屁。
当时钩子还垂涎她的美色,希望趁此机会得到铃儿,但是倔强的铃儿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她之所以拒绝他,首先是因为自己不想堕落成为那样的人,其次是因为她也知道钩子只是一个小喽啰,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当天晚上,她回到宿舍,一边伤心欲绝地痛哭,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难过,同时她也在一边不停地思考着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救铃儿。
想来想去,她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与其说是一个办法,不如说是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梅医生。
铃儿知道,小玉表面上是梅医生的贴身保镖,其实小玉是梅医生一手带大的,梅医生视小玉如同自己的儿女。
梅医生在病院内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权威,她的权利几乎是在院长一人之下,数百人之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众人显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潜规则。
而且,她和院长的关系本身就非比寻常,神秘且隐晦,两人几乎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凭借小玉和梅医生的关系,再凭借梅医生和院长的关系,相信救出小玉也只是一句话的事情,就算不立马救出,至少也能洗清她的罪名。
铃儿相信并且坚信小玉绝对不是杀人凶手!
于是,铃儿连夜出门,去找梅医生和院长,但出了门之后,她才忽然想起来,梅医生和院长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在病院中,他们都在地底下,和那些神秘的黑衣人们一起做着某种神秘的研究。
铃儿在病院内晃荡着,哭声回荡在雨夜中。
她披头散发,神情恍惚,如同孤魂野鬼。
或许是她的哭声感动了上苍,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她在一处草丛中忽然发现了一个井盖。
看见那个井盖的时候,她突发奇想,既然院长和梅医生都在地底下,那只要能进入地下,里面肯定有通道和暗门,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他们。
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救出小玉!
她一想到能够救小玉,就疯了一样地拨弄着井盖的大锁。
她似乎失去了理智,根本就没有想过就算是进入了下水道,又如何能够找到院长他们呢……
她在雨中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开那把锁,她急匆匆返回宿舍,从工具房中偷了一把巨大的铁钳,提着它又返回了井盖旁边。
“咔嚓!咔嚓!”她用铁钳夹着大锁,夹了几十下之后,终于将锁弄断了。
她掀开井盖,没有多想,便钻了进去。
其实,在见到井盖之前,她几乎就要绝望了,是这个突然出现井盖给了她一个机会,给了她一个希望,让她不至于在小玉没死之前就率先放弃了。
她钻进下水道,疯狂地往前钻,疯狂地往地下钻,她相信只要不停地在地下穿梭,总会遇到院长和梅医生他们所在的地方。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个办法虽然愚蠢,但却非常实用。
她一路攀爬,最后竟然阴差阳错来到了一处铁门面前,她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转动转轮,将生锈的铁门打开,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通道里有光,她顺着光芒往前走。
她在弯弯曲曲的管道之间走了很久很久,久得她已经快要忘记了时间的概念,久得她自己都迷失了方向。
她的体能已经消耗殆尽,她颓然地坐在了地上,她衣衫破碎,脸上血迹斑斑,她的呼吸紊弱,身上没有了一丝的力气。
废了这么大的劲,走了这么远的路,爬过了一条条管道,穿过了一道道铁门,来到了地下之后,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她要找的人。
她绝望地流下了眼泪,她用最后一丝的力气哭喊了出来——
她痛苦不甘尖叫声在管道内盘旋回荡,像是一首凄婉的歌。
或许是这首歌起到了作用,或许是她最后的祈祷起到了作用,在她的双眼即将闭上之前,她似乎听见了一阵脚步声自远处响起,脚步声不急不慢,节奏分明……
她用手掌奋力地敲着管道,发出微弱的声响,这声响小的连她自己都听不到。
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沿着管道朝她走来……
她眯起眼睛,看到了一张模模糊糊的脸——他似乎没有脸,不,他的脸上带着一张面具,一张黑白相间的骷髅面具。
这个人正是院长!
她找到了,她终于找到了——
她兴奋地想要叫喊,可是喉咙里像是堵了个东西,根本喊不出声音。
她想要从地上站起来,可是手上却使不出一丝的力气。
她想要用力睁大眼睛看得清楚一点,可是眼皮却越来越沉,上面好像挂着一块铅。
终于,她合上了眼睛。
最后一眼,她看见矮人院长走到了她的跟前,蹲下身子,用手扶住了她的脑袋。
随后,她的头一歪,倒在了他的身上。
矮人院长伸出一只手,挽起了铃儿散落在额前的长发,缓缓擦掉了她脸上的血迹。
一张美丽的脸庞展露了出来。
她的表情带着一丝哀伤,她的嘴角微微上扬,暗藏倔强。
她似乎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
矮人院长面具后面那双古井不波的眼睛逐渐发生了变化。
面具挡住了他的脸,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似乎有些激动。
“有些事,果然是天注定。”
矮人院长自言自语,微微抬头,看了一眼上空。
他没有看见天,上空是钢筋水泥。
矮人院长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铃儿的时候,那是铃儿刚来这家病院第一天,她偷偷地给赵直送内裤,送的还是一条女式蕾丝内裤。
矮人院长当场就揭穿了她的行为,不仅没收了她的内裤,还用一句杀伤力很强的话差点摧毁了铃儿脆弱的神经和柔弱的心脏。
那时候,他盯着铃儿的双眼,将她的善良行为说成是放浪行为,他说:“你是个荡妇!”
时隔半年,她真的成为荡妇了吗?
没有!
但是,她成了别的样子,她早已不是那个见了人就笑,举止文雅,言行得体的大家闺秀了。
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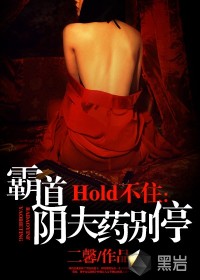


![[生活大爆炸]Miss Zhou的漫漫理科路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19/198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