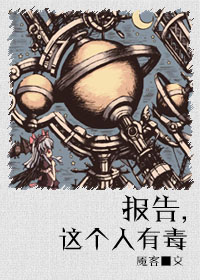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忠诚受到表扬;第二,自费出版各种公益作品,例如……(他提到《酿造苹果酒》的论文;送法兰西学院的绒毛蚜虫报告;《统计大全》,甚至他考药剂师资格的论文);还不提好几个学术团体的会员资格(其实他只参加一个)。
“说到底,”他打了一个转身,高声说道,“就凭救火这一件事,我也该受到表扬呀!”
于是奥默对有权有势的人物低头哈腰。他在选举时不出头露面,却帮了州长的大忙。他最后卖身投靠,辱没人格。他甚至给国王写了一封请愿书,求他“主持公道”;他称呼他为“我们的好国王”,并且把他比做亨利四世。
每天早上,药剂师急着看报,想看到他的提名,但是他的大名老不出现。最后,他等得不耐烦了,就把花园里一块草地剪成宝星勋章的形状,还把上方两行草搞成绶带模样。他两臂交叉,在草地周围转来转去,心中默默念叼:政府有眼不识泰山,世人忘恩负义。
由于尊重死者,或者是由于一种于心不忍的感情,夏尔从来没有打开过艾玛生前常用的那张红木书桌的抽屉。一天,他坐有桌前,到底转了一下钥匙,打开了弹簧锁。莱昂的情书全都出现在他的眼底下。这一回,不能再睁开眼睛做瞎子了!他迫不及待地一直看到最后一封信,搜遍了各个角落,每件家具,全部抽屉,躲在墙后面,又是啜泣,又是号叫,丧魂失魄,简直疯了。他找到一个盒子,一脚踢个头通底落。情书散了一地,中间有张罗多夫的画像,赫然在目。
大家奇怪他怎么这样心灰意懒。他不再出门,也不见人,甚至连病人也不去看了。于是大家以为他在“关起门来喝酒”。
有时,爱打听的人踮起脚来,从花园的篱笆上头向里一望,就会大出意外地看到一个胡子很长、衣服很脏、样子很可怕的男人,在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
夏尔晚上,他牵着小女儿到墓地去。他们到天黑才回家,广场上除了比内的天窗以外,没有灯光。
然而他的痛苦感并没有人分担,未免显得美中不足;他去看过勒方苏瓦大娘,想谈谈“她”。但旅店老板娘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她和他一样。也有自己的苦恼,因为勒合先生到底也开了一家“便利经商”的车行,而伊韦尔因为办事得力。有口皆碑,又要求额外增加工资,否则,他就威胁要“改换门庭”了。
一天。夏尔到阿格伊市场去卖马——这是他山穷水尽,最后一着了——碰到了罗多夫。
冤家碰头,脸都白了。罗多夫在艾玛下葬时只送来了一张名片,所以一开头就含含糊糊地道歉,后来居然胆大脸厚,(那时正是八月,天气很热)请他到小酒店去喝一杯啤酒。罗多夫坐在夏尔对面,胳脯肘放在桌上,一边嚼雪茄烟,一边聊天;夏尔面对着这张她爱过的脸孔,茫然若失,浮想联翩。他似乎又见到了她的一部分。说来令人叫绝,他恨不得自己是罗多夫才好。
罗多夫继续谈庄稼,牲口,肥料,找些无聊的话来填空补缺,唯恐漏出一点私情来。夏尔并不听他的;罗多夫也看得出,他一见对方面部的表情,就找得到回忆的踪迹。夏尔的脸渐渐胀红了,鼻孔震颤得越来越快,嘴唇哆嗦得越来越厉害;有一阵子,他阴沉的脸孔充满了愤怒,眼睛死盯着罗多夫,吓得他话也说不出口了。还好,不消多久,他险上又恢复了那种心灰意懒、死气沉沉的表情。
“我不怪你,”他说。
罗多夫一言不发。夏尔双手抱头,用有气无力的声音,用万分痛苦、无可奈何的语调接着说:
“不是,我现在不怪你了!”
他又加了一句,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豪言壮语:
“一切都要怪命!”
罗多夫这个命运的主宰,看见他到了这步田地还说这种话,未免窝囊得可笑,甚至有点可耻。
第二天,夏尔走到花棚下,坐在长凳上。阳光从格子里照进来;葡萄叶在沙地上画下了阴影,茉莉花散发出芳香,天空是蔚蓝的,斑蝥围着百合花嗡嗡叫,夏尔仿佛返老还童,忧伤的心里泛滥着朦胧的春情,简直压得他喘不出气来。
七点钟,一下午没见到他的小贝尔特来找他吃晚餐。
他仰着头,靠着墙,眼睛闭着,嘴巴张开,手里拿着一股长长的黑头发。
“爸爸,来呀!”她说。
以为他是在逗她玩,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却倒到地上。原来他已经死了。
三十六小时后,应药剂师的邀请,卡尼韦先生赶来了。他解剖后,找不到什么病。
财产卖完之后,只剩下十二法郎七十五生丁,给包法利小姐做路费,投靠老祖母去。老奶奶当年也死了,卢奥老爹已经瘫痪,只好由一个远房姨妈收养。姨妈家里穷,为了谋生,就把她送到纱厂去做童工。
自从包法利死后,接连有三个医生到荣镇来,但都站住脚,不久就给奥默先生挤垮了。他的主顾多得吓人,当局不敢得罪他,舆论包庇他。
他到底得到了十字勋章。
…… 全书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