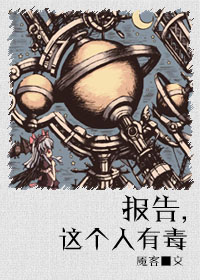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佣人进来了,他只好住口,以免有失体统。费莉西把架子上的杏子放回到篮子里去,夏尔要她拿过来,也没注意他太太的脸红了,拿起一个杏子就咬。
“啊!好吃极了!”他说。“来,尝尝看。”
他把篮子送过去,她轻轻地推开了。
“闻闻看,多香呵!”他把篮子送到她鼻子底下,一连送了几回,还这样说。
“我闷死了!”她跳起来叫道。但她努力控制自己,胸口感到的抽紧就过去了。
“这不要紧!”她接着说,“这不要紧!是神经紧张!你坐你的,吃你的吧!”
因为她怕人家盘问她,照料她,不离开她。
夏尔听她的话,又坐下来,把杏核吐在手上,再放到盘子里。
忽然,一辆蓝色的两轮马车快步跑过广场。艾玛发出一声喊叫,往后一仰,笔直倒在地上。
事实是,罗多夫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到卢昂去。但从于谢堡左比希,只有走荣镇这条路,他不得不穿过镇上,不料他的车灯像电光一般划破了苍茫的暮色,给艾玛认出来了。
药剂师听见医生家乱哄哄的,赶快跑了过来。桌子,盘子都打翻了;酱呀,肉呀,刀呀,盐呀,油呀,撒得满房间都是;夏尔高声求救;贝尔特吓得只是哭;费莉西用发抖的手,解开太太的衣带,艾玛浑身上下都在抽搐。
“我去,”药剂师说,“我到实验室找点香醋来。”
然后,等她闻到醋味,睁开了眼睛,他说:
“我有把握,死人闻了也会活转来。”
“说话呀!”夏尔说,“说话呀!”醒一醒!是我,是你的夏尔,爱你的夏尔!你认出来了吗?看,这是你的小女儿:亲亲她吧!”
孩子伸出胳膊,要抱住母亲的脖子。但是艾玛转过头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不要,不要……一个人也不要!”
她又晕了过去。大家把她抬到床上。
她躺着,嘴唇张开,眼皮闭紧,两手放平,一动不动,脸色苍白,好像一尊蜡像。两道眼泪慢慢地流到枕上。
夏尔站在床头,药剂师在他旁边,保持肃静,若有所思,在这严重时刻,这样才算得体。
“放心吧,”药剂师用胳膊碰了夏尔一下说,“我想,危险已经过去了。”
“是的,她现在安静一点了!”夏尔看她睡着了才说。“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她又病倒了!”
于是奥默问起病是怎样发的。夏尔答道:她正在吃杏子,突然一下就发病了。
“这真少见!……”药剂师接着说。“不过也很可能是杏子引起昏迷的!有些人生来就对某些气味敏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无论从病理学或从生理学观点来看,都值得研究。神甫都懂得这个问题重要,所以举行宗教仪式总要烧香。这就可以使人麻木不仁,精神恍惚,尤其是对脆弱的女人,比对男人还更容易起作用。比方说,有的女人闻到烧蜗牛角或者烤软面包的味道,就会晕倒……”
“小心不要吵醒了她!”包法利低声说。
“不单是人,”药剂师接着说,“就是其他动物也有这种反常现象。你当然不会不知道:荆芥俗名叫猫儿草,对猫科动物会产生强烈的春药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举一个确确实实的例子,我有一个老同学布里杜,目前在马帕卢街开业,他有一条狗,只要一闻到鼻烟味,就会倒在地上抽搐,他还在吉约林别墅里,当着朋友们的面做实验。谁想得到使人打喷嚏的烟草,居然会摧残四足动物的机体?你说这是不是奇闻?”
“是的,”夏尔没有听,却随口答道。
“这就证明了,”药剂师自己得意,却又不伤害别人,笑嘻嘻地说,“神经系统有无数不规则的现象。关于嫂夫人呢,说老实话,我觉得她是真正的神经过敏。因此,我的好朋友,我不劝你用那些所谓的治疗方法,那是借口对症下药,实际上却是伤了元气。不要吃那些不中用的药!只要注意调养,那就够了!再用点镇静剂,软化剂,调味剂。还有,你看要不要治治她的胡思乱想?”
“在哪方面?怎么治法?”包法利问道。
“啊!问题就在这里!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这就是问题了!’我最近看到报上这样就。”
但是艾玛醒了,喊道:
“信呢?信呢?”
大家以为她是胡言乱语;从半夜起,她就精神错乱了,恐怕是得了脑炎。
四十三天来,夏尔都没有离开她。他不看别的病人;他自己也不睡觉,只是不断给她摸脉,贴芥子泥膏,换冷水纱布。他派朱斯坦到新堡去找冰;冰在路上化成水了,他又派他再去。他请卡尼韦先生来会诊;他把他的老师拉里维耶博士也从卢昂请来;他急得没办法。他最怕艾玛虚弱得精疲力竭了,因为她不说话,也听不见,看起来甚至不痛苦——仿佛她的肉体和灵魂在万分激动之后进入了全休状态。
十月中旬,她可以在床上坐起来,背后垫了几个枕头。夏尔看见她吃第一片果酱面包的时候,哭了起来。她的力气慢慢恢复了,下午可以起来几个小时。有一天她觉得人好些,夏尔还让她扶着他的胳膊,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小路上的沙子给落叶遮住了,她穿着拖鞋,一步一步地走着,肩膀靠住夏尔,脸上带着微笑。
他们这样走到花园尽头,平台旁边。她慢慢地挺直了身子,用 手搭成凉篷,向前眺望;她向前看,尽量向前看,但只看见天边有几 大堆野火,在远山上冒烟。
“你不要累坏了,我亲爱的,”包法利说。他轻轻地把她推进花棚底下:
“坐在这条长凳上,舒服一点。”
“啊!不坐!不坐!”她有气无力地说。
她一阵头晕,从晚上起,病又发了,说不准是什么病,反正更复杂了。她有时是心里难受,有时是胸口,有时是头部,有时是四肢,有时还呕吐,夏尔以为这是癌症初发的症像。
可怜的男人,除了治病以外,他还得为钱发愁呢。
第十四节
首先,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还得清奥默先生的医药费,虽然作为医生,他可以不付药钱,“啊!我的确认识!片似的飞来,送货的商贩口出怨言,尤其是勒合先生叫他头痛。的确,在艾玛病得厉害的时候,勒合抓住机会,乱开发票,急急忙忙送来披风,旅行袋;一只箱子外加一只,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夏尔说他用不着这些,但没有用,商人气势汹汹地说这都是夫人订的货,出门不能退换;再说,不能和夫人过不去,不利于她复原,所以要先生考虑;总而言之,他决心打官司也不放弃他的债权,退回他的货物。后来夏尔要把东西送回他的商店去,费莉西却忘了送;夏尔一忙,也没再想到这件事,不料勒合又来讨债了,又是恐吓又是诉苦,逼得包法利只好写了一张为期半年的借据。但他刚在借条上签字,就起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何不向勒合先生借一千法郎?于是他露出了为难的神色,问他有没有办法帮忙,还说借期一年,利息倒不在乎。勒合跑回铺子,拿来了金币,要包法利再写一张借据,说明年九月一日,付清欠款一千零七十法郎,加上原欠一百八十法郎,合计一千二百五十法郎整。这样一来,六分利息,加上四分之一的佣金,还有卖货起码有三分之一的赚头,一年期满,就可以净得一百三十法郎的好处;而他希望生意并不是到此为止,借据到期不付现款,还要利上加利,那么他小小的资本,吃医生的,喝医生的,就像在疗养院里一样,等回到他身边的那一天,恐怕吃得要撑破肚皮,胖得要撑破钱袋了。
再说,他一切顺利。他投标供应苹果酒给新堡医院,又得了标;吉约曼先生答应他入股,得到格鲁默尼泥炭矿的股份;他还打算在阿格伊和卢昂这条路上加开一趟班车,跑得快,票价低,运货多,不消说会挤垮金狮旅店的老马破车,那么,荣镇的生意就全落在他手里了。
夏尔好几次自己问自己:明年有什么办法还这么多债?他挖空心思,想出主意,比如说找父亲帮忙,或者是卖东西。但父亲不会理他,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想起来都不愉快,于是干脆不想算了。他反责备自己不该忘了艾玛;仿佛他的思想都只属于这个女人,一刻不思量,就等于偷了她的东西一样。
冬天过得艰苦。太太复元的时间拖得很长。天气一好,就把她坐着的扶手椅推到窗前,眺望广场,因为她现在对花园有反感,那边的窗帘总是放下的。她要人把马卖掉,她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都讨厌了。她的思想似乎只限于调养自己。她坐在床上吃点心,拉铃叫女佣人来,问汤药熬好了没有,或者是和她谈谈天。那时,菜场棚子顶上的积雪把一片茫茫的白光反射到她房里;过些日子,天又下起雨来。艾玛每天都带着渴望的心情,等待必定会发生的小事,虽然事情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燕子号班车在傍晚回到荣镇,那时,老板娘高声喊叫,别的声音此呼彼应,而伊波利特的手提灯,像黑暗中的星光一样,在车篷上寻找行李箱子。夏尔中午回家,下午出去;然后,她喝一碗汤,到五点钟天要黑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了,拖着木鞋在人行道上踢踢蹋蹋地走,都用手中的尺于敲打一扇又一扇档雨的窗板。
就在这个时候,布尼贤先生来看她。他问她的健康情况,和她谈谈新闻,并且劝她信教,他谈起来又随便又温存,倒不显得枯燥无聊。一看见他的黑道袍,就能给她安慰。
有一天她病得最厉害的时候,她以为自己不行了,要求举行临终前的宗教仪式。人家在她房里作后事的准备,把堆满药瓶的衣柜改成圣坛,费莉西在地上撒大丽花,这时,艾玛觉得有股力量经过她的身上,使她摆脱了痛苦、知觉、感情。她的肉体轻飘飘的,不再思想,新的生命开始了;她觉得她的灵魂飞向上帝,就要融入对天国的爱,正如点着的香化为青烟一样。床单上洒了圣水;神甫从圣体盒中取出白色的圣体饼,她伸出嘴唇,领受救世主的圣体时,感到天堂的幸福使她昏迷沉醉。她床上的帐子微微鼓起,好像周围缭绕的祥云,衣柜上点着两支蜡烛发出的光线,在她看来,似乎成了耀眼的光轮。于是她又让头倒下去,以为听见了天使在天上的歌声琴音,在一片蔚蓝的天空中,看见了光辉灿烂、崇高庄严的天父,坐在黄金的宝座上,在手拿绿色棕榈枝的圣徒中间,示意长着火焰翅膀的天使下凡,伸出胳膊,把她接上天去。
这个光辉的幻觉留在她的记忆里,就像一个最美丽的梦想;直到现在,她还可以努力追寻当时的感觉,虽然现在不能心无杂念,但是还能体会到同当时一样深入心灵的脉脉温情。她的心灵给争强好胜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才领会到了基督教的谦逊精神。艾玛尝到了弱者的乐趣,就在自己身上摧毁意志,好空出地盘,让怜悯来占领。原来尘世的幸福之外,还有一种更伟大的幸福;尘世的情爱之上,还有一种更伟大的博爱,无边无际,没完没了,而且不断增长!在她的希望造成的幻像中,她隐约地看到一个纯净的幻境,和天界打成一片,而这正是她的向往。她要成为一个圣徒。于是她买念珠,戴护身符;她要在卧房的床头挂一个镶绿宝石的圣物盒,以便她每天晚上顶礼吻拜。
神甫对艾玛的这份诚心觉得惊异,虽然他也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