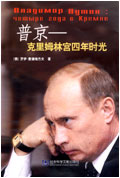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谢你,罗曼诺夫!
没有我,你究竟怎么过得了,我的大尉?那声音咯咯笑着。尽管你那么聪明,
但有时也会是个最愚蠢的人。
瓦吐丁看到有什么东西变了。双眼一眨,变清亮了,那疲倦老朽的背挺直起来。
是什么在支撑你?憎恨?为了你家庭发生的事情你就那么痛恨祖国……或者是
别的什么?……
“告诉我,”瓦吐丁说:“告诉我,你为什么憎恨祖国。”
“我不恨,”费利托夫答,“我曾为祖国杀敌。为祖国流过血。我为祖国被烧
伤了。但我不是为了你的同类做这些事情。”尽管他那样虚弱,轻蔑之情象火焰一
样在他眼中燃烧。瓦吐丁不为所动。
我接近了,但什么东西变了。如果我能找出那是什么,费利托夫,我将制住你!
某种东西告诉瓦吐丁,他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窍门在于认准它。
审讯继续下去。虽然费利托夫这次会成功地进行抵抗,以及下一次,以至于再
下一次,瓦吐丁正在榨干那人的肉体和情感能量。两人都知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在一件事上两人都错了。两人都以为瓦吐丁控制着时间,纵然时间是人的最高
主宰。
格拉西莫夫因美国新到的“火急”电文而吃了一惊,这一份来自普拉托诺夫。
它是通过电缆发来的,提示他在外交信袋中有一道“仅供主席阅读”信息在途中。
那真是非同寻常。克格勃比其他的对外情报机构更依赖一次性使用密码系统。这些
是不可破译的,甚至在理论上也不能,除非密码序列本身被破获了。它是缓慢的,
但却是稳当的,而克格勃需要的就是“稳当”。然而,在那一级传送之上,有另一
套规程。每一个主要情报站都设有—种特别密码。它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不过是从
“驻扎官”直达主席。普拉托诺夫非常重要,连中央情报局都没有怀疑到那种程度。
他是华盛顿的驻扎官,情报站站长。
那份电文到达时,直接送到了格拉西莫夫的办公室。他的私人密码文书,一个
无懈可击的大尉不在办公室。主席自己动手,译出第一句,得知这是一个“鼹鼠”
警报。克格勃没有一个固定的术语来描述自己内部的叛徒,不过高级官员知道那个
西方词。
这份电文很长,花了主席整整一小时来解密,在解译用三十三个字母的俄语字
母表任意移换组成的内容时,他为自己的笨拙而骂声不绝。
一个潜伏特务在克格勃内部?格拉西莫夫吃惊地想。地位多高?他传进他的私
人秘书,要代理人卡休斯和中央情报局的瑞安,I ·P ·〔瑞安名的字母缩写,似
为俄语化的,如John转为Ivan缩为I 。——译者〕两人的档案,跟所有这类命令一
样,它没有用多长时间。他暂时把卡休斯的放到一夯,打开了瑞安的档案材料。
有一份六页的生平简历,仅在六个月前刚更新过,加上原版报章剪辑和翻译稿。
他不需要后者。格拉西莫夫讲一口带口音而可接受的英语。他读到:年龄三十五,
资历涉及商业界、学术界,以及情报界,驻伦敦的特别联络官。他在捷尔任斯基广
场的第一份简短评价带上了某位分析专家政治观点的色彩,格拉西莫夫看得出来。
一个富有而吃不了苦的半瓶醋。不,那不对头。他上升得太快,不可能是那样,除
非他有在档案中显然不存在的政治影响。可能是个聪颖的人——一个作家,格拉西
莫夫看到,记起在莫斯科有他的其中两本著作的印册。肯定是个骄傲的人,习惯于
舒适和特权。
那么说你犯了美国的货币流通法,是吗?于对克格勃主席,这个想法来得很容
易。在任何社会,腐化都是迈向财富和权力的路。瑞安有他的缺陷,正如所有人那
样。格拉西莫夫知道他本人的缺陷就是极端的权力欲,然而他把对任何次要事物的
欲望看成是一个傻瓜的标志。他回到普拉托诺夫的电文。
“评价,”信文作出结论,“对象不是为意识形态或金钱的考虑所动,而是为
愤怒和自我形象。他有一种对监狱的真实恐惧感,但更怕的是身败名裂。I ·P ·
瑞安可能掌有他声称的情况。如果中央情报局的确有一个置身高位的‘鼹鼠’在莫
斯科中心内,瑞安很有可能看到过来自他的情报,即使没见过名字或脸相。情报应
该足以辩明这个漏洞。”
“建议:因两个原因,应该接受这项提议。第一,识破美国间谍。第二,将来
好利用瑞安。这次提供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有两方面。如果我们去掉对对象不利的证
人,他就欠了我们的债。如果这项行动被发现,可以怪罪于中央情报局,由此而来
的质询将会严重地损害这个美国情报机关。”
“嗯,”格拉西其夫对自己喃喃而语,一边把档案放到一旁。
代理人卡休斯的档案厚得多。他这时正在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最好的情报来源。
格拉西莫夫把这个档案读过几次了,只是快速翻阅,直到他翻到最新近的情况。两
个月前,瑞安受到了调查,详情不知——卡休斯把它当作未经证实的传言来报告。
那是对它有利的一点,主席心想。它也排除了瑞安的提议同别的任何最近发……
费利托夫?
要是那个瑞安能辩明的地处高位的特务是我们刚刚逮捕的那个怎么办?格拉西
莫夫心想。
不。瑞安本人在情报局内的位置就够高的了,不至于把政府部门搞混淆。唯一
的坏消息是克格勃高层有一漏洞,这事不是格拉西莫夫眼下需要的。它的存在就够
坏的了,不过让消息传出大楼……那可是场大灾难。如果我们发起一场真正的调查,
风声就会传出。如果我们不找出我们中间的特务……并又如果他如这个瑞安说的那
么地处高位……要是情报局发现我和阿列克山德罗夫……?
他们会干什么?
要是这个……?
格拉西莫夫微笑着,向窗外看去。他会思念这个地方的。他难合这种游戏。每
一个事实至少有三面。每一种想法有六面。不,如果他要相信那个的话,那么他必
须相信卡休斯在情报局控制之下,而且所有这一切在费利托夫被逮捕前就计划好了。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查阅他的日历,看美国人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次将有
更多的社交活动。如果美国人真的决定把他们的“星球大战”〔即战略防御计划的
通俗、戏谑说法。——译者〕系统摆到谈判桌上——那会使纳尔莫诺夫总书记脸上
增光,但那会改变多少政治局票数?不会太多,只要我能将阿列克山德罗夫的顽固
控制住。而且如我能显示我已招幕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特务,在中央情报局内如此之
高……如果我能预测美国人将交易掉他们的防御计则,那么我本人就能抢在纳尔莫
诺夫的和平倡议前……
决定作出了。
然而格拉西莫夫不是一个爱冲动的人。他发出一个信号给普拉托诺夫,要通过
代理人卡休斯查实一些细节。这个信号他可通过卫星来传。
那个信号一小时后到达华盛顿。它及时地被苏联大使馆和美国国家安全局从苏
联“光谱”-19通讯卫星抄录下来,安全局把它输进计算机带子,同其它成千上万
的俄国信号在一起,安全局为了破译这些信号,一天到晚连轴转。
对苏联人要容易些。信号被带到使馆的一个保密部分,在那儿,一个克格勃尉
官把加密搅乱的字母转化成清晰的明文内容。然后它被锁进一个有守卫的保险箱,
等普拉托诺夫早晨来。
那发生在六时三十分。通常的报纸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想,美国新闻界对克格
勃真是很有用处。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的概念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他甚至从来没有
考虑过它的真正功能。不过其它事情要先干。夜间执勤官在六时四十五分时进来,
向他汇报前一夜的事情,而且也交付了来自莫斯科的信息,那儿现在已经是矢后时
分。在电文清单上头一条是一个仅供驻扎官阅读的通知。普拉托诺夫知道那必定是
什么,立即朝保险箱走去。保卫使馆这一部分的那个年轻克格勃军官一丝不苟地检
查普拉托诺夫的证件——他的前任由于大胆得在仅仅九个月后就假定他凭眼睛朗认
得普拉托诺夫而失掉了这份工作。这份电文,在一个密封套内恰当地标明,放置在
恰当的分类格内,普拉托诺夫把它塞进衣袋,然后把门关上锁牢。
克格勃的华盛顿情报站比情报局在莫斯科的要大,然而还大得不够使普拉托诺
夫满意,原因是在这个使团的人数被削减到数量上同美国在苏联的大使馆配员相当
的程度,美国人花了多年时间才做到。他通常在七时三十分传他的下属长官们到他
们的晨会,但是今天他提前叫了他的一个军官。
“早上好,上校同志,”那人端正地说道。克格勃不以它的诙谐而著称。
“我需要你从卡休斯那里得到一些关于这个瑞安事宜的情况。我们绝对有必要
尽快地核实他目前的法律困境。那就是说,今天,如你能办到。”
“今天?”那人接过书面指示的时候,有些不安地问道:“行动这么快是有危
险的。”
“主席知道那点,”普拉托诺夫冷冰冰地说。
“照办,”那人点头同意。
那人寓去时,驻扎官暗暗地笑了。那就是一个月里他所表露的感情。这一回真
是有前途。
“鲁汉在那儿,”一个联邦调查局专员说,这时那人从使馆大院内出来了。他
们当然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过第一个跟踪他的专员注意到他象一个粗鲁的家伙,
这名字就固定了。他的正常早程式表面上是开几间使馆办公室,然后在高级外交人
员九点钟出现之前处理零碎事务。那包括在一家附近的咖啡店吃早餐,买几份报纸
杂志……而且常常在几个地点之一留下一两个记号。就跟大多数反谍报行动一样,
真正的难点是得到第一个突破点。在那之后就是纯粹的警察工作。他们十八个月前
就获得了对鲁汉的突破点。
他走过四个街区到了那家店子,在冷天里穿戴得不错——他可能发觉华盛顿的
冬天相当温和,他们一致这样认为——并且正按日程表拐进那地方。跟大多数咖啡
店一样,这家有一批常客。其中三人是联邦专员。一人的穿着象一个女商人,总是
在一个角落的隔档座位里独自一人读着她的《华尔街日报》。两人拴着匠人的工具
带,或在鲁汉进入前,或在后,昂首阔步朝柜台走去。今天他们在等他。当然他们
不总是在那儿。那个妇女,特别专员黑丝尔·卢米斯,把她的日程同真正的商事协
调起来,注意在工假日时不出现。那是一个风险,但是一项严密的监视,不管制定
得有多仔细,不能够太有规律。同样地,在他们知道鲁汉不在的日子里,他们也出
现在那家咖啡馆,从不改变他们的程式来显示他们对监视对象的兴趣。
卢米斯专员在一篇文章的边上记下了他的到达时间——她总是在报上写划——
而木匠们从柜台后面的镜面墙里看着他,一边狼吞虎咽,吃着他们的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