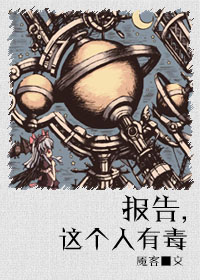地下人-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在书桌旁坐下,双膝伸人桌下容膝的空间里,拨电话到麦威里位于旧金山吉利街的办公室去。值班的女孩把我的电话转接到他住家大楼的顶层去。
电话是另一个女孩接的,声音比较不那么一本正经,然后是麦威里接过去。
“亚契,等下再打给我。我正在跟女孩子快活,你在破坏我的好事。”
“那你打来。”
我把卜贺太太家的电话号码念给他记下。
然后我拿起电话机,把压在下面的那个皮面文件匣打开。文件匣里头有几张大页的书写纸,还有一张用墨水画成的褪色地图,地图的纸已经起皱变黄。地图上画出了一半左右的圣德瑞莎海岸平原,后面还轻描上几笔山丘和山群,看来很像是拇指印和掌印。
有人在地图的右上角写道:“美国土地局圣德瑞莎市前使节费康南。一八六六年六月十四日于办公室存档。约翰·贝利”
书写纸的第一页内容是伊莉·费康南·卜贺以斯宾塞书法写的(美国俄亥俄州斯宾塞氏所创的草书体。为十九世纪五○~八○年代间美国最流行的书法指南),题目是“回忆”,我读了出来:
圣德瑞莎郡历史协会要我为我的家族历史记上几笔。我的祖父罗伯·杰可·费康南,是麻萨诸塞州一位学者之子,他是商人,也是路易斯·阿刚西斯的受业弟子。我祖父曾经参加过美国联军,于一八六三年五月三日昌色拉维尔一役中受到重伤,几乎殉职。不过他终究得以终老,亲口告诉了我他的这段经历。
后来他来到太平洋海岸养伤。一方面通过买卖,一方面经由婚姻,他攒聚了好几百亩地的产业,也就是后来人称的费康南农场。这块农场大半原是教会的属地,于一八三四年归于民用,成了大墨西哥区的一部分;而后从我祖母手中传给我祖父,之后再传给我父亲,费康南二世。
要我提笔描述我已故的父亲,对我来说诚非易事。他是费康南家族当中第三个读哈佛大学的男孩。说他是个农场主人或是生意人,不如说他更像个自然学家和学者。我的父亲曾经遭人批评,说他败尽家产,而他总以“人生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事要做”以为回覆。他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的业余鸟类学者,圣德瑞莎地区第一本本地鸟类品种目录就是他的作品。他克藏丰富,本土和异国皮羽都有,后来都成为圣德瑞莎博物馆鸟类收藏品的主要项目。
从这里开始,那笔斯宾塞书法开始歪斜:
我听过不实的传言,说我父亲是个残忍的鸣禽凶手,说他之所以杀害这些鸣禽,是出于他嗜杀的本性。没有比这个更离谱的谎言了!他射杀鸟儿纯粹是为了科学,是为了保存它们身上短暂如春花的斑点、条纹之美。他深爱这些色彩斑烂的小飞行者,但为科学之故,他不得不射杀它们。
我可以以我个人的观察作证。我陪我父亲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探险,多次看到他把中弹的啭鸟或是鸣鸟握在他温柔而刚毅的手里,对着它穿孔的身躯毫不隐饰地哭泣。有时候我们两个,就我和他,会躲在我们家族拥有的峡谷某个阴林处一同哭泣。他是个好人,也是个神枪手,他射死鸟儿的时候快如迅雷,完全不留痛苦,也从不失误。费康南二世,其实是个戴着人类形貌下凡的神。
到最后,字迹已经变得碎碎片片,纠结在划了线的黄色纸页上,有如溃不成军的行伍。
我开始搜索书桌的抽屉。右手边第一个抽屉里塞满了帐单,其中有几张已经好几个月没付清,上面印有小小的字样:“请立刻付款”。“如果再行拖欠,我们将会诉诸法律”。
我在第二个抽屉里找到一个老旧的木制枪匣,我打开它,一对德国打靶用手枪摆在尺寸适中的软缎座上。枪的式样虽老,可是上过油擦得晶亮,看来像是珍奇的蓝色珠宝。
我从木匣里拿起一枝枪,放在手里掂了掂。又轻又平衡,这枪似乎本身就为配合眼睛视线而设计,我不由得跟着它瞄准。我用枪对准照片里那个蓄着山羊胡的人,可是徒觉愚蠢。我带着枪走到窗边,想找个比较好的目标瞄准。
外面没有鸟儿。不过水泥柱的金属顶座上有个圆形的喂鸟器,一只老鼠正在吃喂鸟器里剩下的几颗谷粒。我举起空枪对准老鼠,那个小东西跑下柱子,消失在黑色的溪谷里。
第20章
第20章
“你到底在干什么!”珍在我背后说。
“玩游戏。”
“拜托,把枪收起来。你动我婆婆的枪,她会不高兴的。”
我把枪放回木匣。
“这对枪很漂亮。”
“我不觉得,我觉得所有的枪都可恨至极。”
她陷入沉默,可是她的眼睛意犹未尽,满满有话要说。这个女人已经把她明亮的短洋装换下,穿上一套并不合身的黑色过膝长衣。她又让我联想起作戏来,只是这次是个年轻女人扮演老者的角色。
“这样穿还可以吗?”
她的声音听来充满焦虑,像是因为儿子不在、丈夫去世了,因此开始怀疑起自己到底是谁。
“你怎么穿都好看。”
她却拒我的恭维于千里之外,仿佛它会枯污了她。她坐回沙发上,把黑裙往下拉,让双腿完全隐盖在裙摆下。
我把枪匣关上收好。
“这些枪是你婆婆父亲的吗?”
“是的,本来是她爸爸的。”
“她用枪吗?”
“如果你的意思是她现在有没有用枪来射杀鸟儿,答案是没有。这些枪是那个伟大人物的宝贵遗物。这栋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像是遗物,我觉得我自己也是。”
“你穿的是你婆婆的衣服吗?”
“是的。”
“你会不会想住在这栋房子里?”
“会吧,这房子现在很适合我的心情。”
她低头以一种倾听的姿态坐着,仿佛那套黑洋装跟太空装一样,浑身都装着通讯的线路。
“我婆婆以前射杀了很多鸟,她也教史丹射鸟。这种事一定让史丹很困扰,否则他不会告诉我。显然他妈妈也很困扰。在我认识她以前,她早就完全收手,再也不射鸟了——可是我爸爸从来没有收手过,”她突然的表白令人意外。“至少在我妈还没离开他以前没有。我爸爸喜欢射东西,只要会动的东西,他都喜欢射。我妈跟我就得替他射杀的鹧鸪还有鸽子拔毛。我妈离开我爸以后,我从来没有回去看过他。”
她的话题从史丹的家庭跳到自己的家庭,一点也没经过转折。我觉得奇怪,于是问她:
“你现在想回娘家吗?”
“我没有娘家。我妈再嫁,现在住在纽泽西。我最后一次听到我爸的消息,是他在巴哈马群岛开钓鱼船。不管怎么说,我没办法面对他们,他们会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到我头上。”
“为什么?”
“他们就是这样,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离开家,自己打工供自己读完大学,而他们两个都不赞成。一个女孩子家应该乖乖听话,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
她的声音冷得像石头,充满了怨恨。
“那你会把所有的过错怪到谁的头上?”
“当然是我自己。不过我也怪史丹。”她又低下眼睛。“我知道这么说很可怕。我可以原谅他跟那个女孩的事,还有他为找他爸爸所做的一切傻事。可是为什么他非得要把龙尼也带走——带去呢?”
“他要向他妈妈要钱,带龙尼去看他妈妈等于是交易的一部分。”
“你怎么知道?”
“你婆婆告诉我的。”
“她的确是会说这种话的人,她是个冷冰冰的女人。”接着,仿佛在对这房子道歉,她又说:“我不应该这样子说她,她受的罪也够多了。史丹跟我都不值得她疼惜,我们一直拿得太多,给的太少。”
“你们拿了她什么东西?”
“钱。”
她听来像是跟自己生气。
“你婆婆很有钱吗?”
“当然,她有钱得很。那件‘峡谷之家’开发案一定让她发了不少财,而且她手上还有好几百亩的地。”
“可是那些地除了几亩酪梨树林之外,生产并不多。而且她好像有一大堆帐单还没付。”
“那是因为她有钱,有钱人从来不付帐单的。我爸爸以前在雷诺开一家卖运动器材的小店,最买得起的人都是那些他必须威胁要告上法庭才肯付帐的人。我婆婆的祖产每年就有好几千块钱的收益。”
“差不多几千块?”
“我不大清楚。她对她的钱口风紧得很。不过她是有钱。”
“如果她死了,钱会归谁?”
“你不要说这种话!”珍的声音听来既害怕又带有迷信。她接着用比较克制的声音说:“简若姆医生说她会好起来的,她这次心脏病发,只是因为过度操劳和压力造成的。”
“她能够正常谈话了吗?”
“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今天就不会去烦她。”
“我去问问简若姆医生,”我说。“不过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如果她死了,钱会归谁所有?”
“龙尼。”她的声音很低,可是身体忍不住紧张激动。“你是担心谁来付你的费用吗?这就是你该去找龙尼,可是却一直赖在这里不走的原因吗?”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坐着保持低姿态好一阵子。愤怒和悲伤像电流一般轮番出现在她身上,她把愤怒的矛头转向自己,把裙子的下摆放在两手中间用力撕扯,像是想把它扯破似的。
“珍,你不要这样。”
“为什么不要?我讨厌这件衣服。”
“那就脱下来换另一套。你绝对不能倒下去。”
“我受不了一直等待。”
“这件事很可能还会拖一阵子,你必须忍耐下去。”
“除了等,我们是不是还能做些别的事?你就不能出去找他吗?
“不能直楞楞地找,地太大,而且水太深。”她看起来失望已极,因此我加上一句:“不过我有一两条线索。”
我再度拿出那则广告,和那张史丹父亲跟柯帕奇前妻的合照。
“你看过这个没有?”
她低下头去看那张剪报。
“广告登出来好一阵子以后我才看到。史丹在《纪事报》上刊广告并没有告诉我,那时候是六月,我们在旧金山。他也没有告诉他妈妈,所以当她看到的时候,她气疯了。”
“为什么?”
“她怪他把这个丑闻重新抖了出来。不过我想,除了她和史丹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在乎。”
还有柯帕奇父子会在乎,我心想,或许那个女人也会。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
“我婆婆说她姓柯帕奇,本来是本地一个叫做莱恩·柯帕奇的房地产商的太太。”
“他跟你婆婆的关系如何?”
“在我看来,他们处得非常好。他们是‘峡谷之家’的伙伴,也可以称为合资人。”
“那他的儿子杰瑞呢?”
“我不认识他儿子。他长得什么样子?”
“瘦瘦高高的,大概十九岁,留一头棕色带红的长发,满脸胡子。很情绪化的一个男孩子,他昨天晚上用一枝枪敲了我的头。”
“他就是那个把龙尼带上船的人?”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