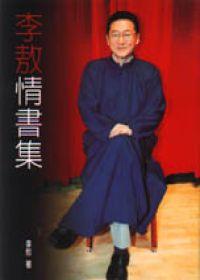清史情书-第7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大段话,一口气说完,喘了口气,他又接着说了,“福晋,您估摸着是看我在这儿,不好意思哭,可是您不应该管我在这儿不在这儿,您想哭就哭,一个人活的是自己的真性情,人间难得一真字,那庙里的菩萨可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见我还是没反应,他往后退了几步,“福晋,看样子您还是顾着面子,那您就自己在这儿哭,等您哭完了,您就会发现,这天可比您看到的蓝,这树,它也不是歪脖子树。”话音刚落,他就扭过身,走了,一边走还一边摇晃着脑袋。
真性情?
不知道是因为听了他这几句话,还是我到了该哭的时候,反正他一走,我就抱着旁边的歪脖儿树哭开了。
我就是从那时候起,改变了对陶之典的印象,他或许就是他说的那种真性情的人吧。
我不是对他的那几句话没反应,而是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岳乐不在家,我只能把自己当成菩萨,我得让这个安王府里所有的人感到安心,我硬撑着把自己的孩子送走,把俞霁送走,把兰儿甘送走,不是不想哭,不是不累,只是想哭,找不到肩膀,累了,也没个依靠,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得变成菩萨。真性情?或许在娘家的时候有,现在没了。
康熙十七年,夏(三)
很奇怪,从那天以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跟陶之典总能在园子里那个角落碰见,刚开始只是浅浅的说几句,主要是说蕴端,后来就聊的多了,聊的多,一是因为他在我面前把那份无礼收了起来,我才可能跟他说下去,二是因为很多年没有人跟我谈什么诗词歌赋了,一时间我的谈兴就被勾了起来,安王府虽不至于要为柴米油盐操心,但是也是家大业大一地鸡毛,以往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去玩那些高雅,也无人陪我去玩那些雅致,如今兰儿甘走了,孩子们也大了,这时间就多了起来。
“福晋,您看这荷花开的怎样?”陶之典坐在荷池旁边的青石上问我。
“不错,古城野水,乔木参天。”我坐在亭子里的石凳上看着荷花,也看着他。
“福晋,乔木参天不错,古城也不错,可是这野水?”他转过头眯着眼睛看我,扇子在左手上拿着。
“姜白石在武陵的那种意境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在这京城尺寸之地哪有野水,看着自己院子里的这一方水,就全当是野水吧。”
“也对。”他扇子一张,扇了两下,转过身,闷闷的问了一句,“福晋知道陶某这辈子最想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
“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他说的也是姜白石念奴娇里的句子。
“好意境!”
“只可惜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他把头转了过来,看了我一眼,我冲他笑笑,其实我不大明白他为什么看我,我的笑完全是基于礼貌。
他见我笑,自己也笑了,身子一拧,站起来,走到亭子里,一转身,坐我对面了。
给他倒了一杯茶,顺着刚才的话说了下去,“陶先生,为什么说青盖亭亭,情人不见呢?尊夫人~”
他没着急回答我的话,把扇子放在石桌上,把我给他倒的茶端起来,但是没喝,只是端着。
“福晋,内人是父母娶的。”
“父母娶的又如何,难道陶先生也想做姜白石二十四桥明月夜,等着玉人教吹箫?”我促狭的说,他说的那句话好像是说妻子不是情人,这个观点我可不大赞同。
“有点儿,只不过找不到而已,不说了,说起来败兴。”他说完这句话才低下头抿了一口茶,刚喝进去就喷了出来,要不是我躲的快,差点儿就喷到我身上。
咳咳,他咳了两声,脸都咳红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能说话,站起身,满脸的不好意思,“福晋,真对不住。”
我吭哧笑了,“陶先生怎么连茶都喝成这样,难不成真的是我刚才说的话败兴至此吗?”
“不不不,”他连忙摇手,急忙解释,“不是,福晋,您这茶是荷花叶泡的?”
“清凉去火。”
“怪不得呢,”他做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前年,小儿给我放的荷花叶,我喝了之后就不舒服,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喝了,刚才一喝之下,失礼了。”
“比起您刚进府的那句同安,这个真的不算什么,坐吧,站着还得让我仰着脖子。”我用手指指对面的石凳,前半句是话里有话。只不过不知道他是真的没听出来还是听出来也能无视,他笑了一下,很利索的坐下了,不见有什么尴尬。
他坐下之后,我没继续说,刚才的谈话要不是他喷出的那一口,估计最后得弄个不欢而散,原因是,他对自己妻子的态度,让我不舒服。想想自己这些年的委屈,我就给他的妻子抱上了委屈,这么一来就觉得谈下去没什么意思,神情就有些懒懒的。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出我的情绪变化,估计是没看出来,他还是很兴趣盎然。
“福晋问了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那福晋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这还是头一次有人问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岳乐都从来没有问过, 既然对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说过的话,我自然也不能对他全盘托出,拿着茶杯把玩了一会儿,才回答道:“女人想过的日子。”
“女人想过的……”
我把他的话截住了。
“陶先生,您刚才说您想过的是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的日子,可是您干嘛要进京呢?”我把话题转了。
他很明显的愣了一下,看样子像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哦了一声之后,才笑着说:“跟王爷说对路了,而且也顺便看看自己多年未见的朋友。”
“朋友?”
他呵呵的笑了一下,“福晋想必知道皇上今年正月下诏中外臣工各举博学通才之人,以备顾问,由皇上亲试的事,那些鸿儒们有一些是我的朋友,借着这个机会我也会会他们,到时候还希望福晋能够给个时间上的方便。”
“鸿儒?我听过,那您难道不是吗?”
“我是,只是我不来。”
“那您怎么还来了安王府?”
“那是我跟王爷说对路了,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只是为了一个对路,譬如说,今天我跟您说对路了,您现在指着这荷花池让我跳,我二话不说立马就跳。”他往外面荷花池那边一指。
“这就是您的真性情?”
“没错!”他把扇子拿起来张开又合上,啪啪的在手里拍着。
“真性情。呵,时间上您自己看,”我想了一会儿,对他说,“只不过,我希望您去看您的那些鸿儒们的时候能带上蕴端。”让蕴端见见那些大家,对他是好事,这是我自己藏的私心,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想让他把孩子们全都带上。
“那是当然,我还没忘了自己对王爷的承诺,我是西席。”说完,自己在那边笑个不停。
我附和着笑了两声,说是附和,那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刚才那句话有什么好笑的。
他看出来了,也说出来了,“福晋,虽然我这人眼神不行,可是我也看的出您刚才的笑不是这儿出来的,”他在自己的胸前比划了一下,摇摇头,“不是真性情。”
“不是人人都可以跟您一样活的潇洒的,这话是真话。”
“福晋,”他身子往前移了移,“王爷不能真性情这我理解,身处朝堂之上,真了只能让别人抓住把柄,可是福晋按说不用管这些呀,您知不知道,您笑起来很漂亮。”
话就在这儿打住了,他的话说的有些出了格。
彼此间一时也就没了话。
沉默是我先打破的,站起来,打了个哈哈,找了个借口,“尊夫人想必也很漂亮,陶先生,来的时候我就跟您说,一会儿府里的账就要送过来了,现在估摸着已经到了,现在要是不看就得看到半夜了,所以真是不好意思,得先走一步了。”
他站起来,自嘲的笑笑,“是,福晋自便。”
在我转进亭子背面时,我听到了他后面说的话,“翠叶吹凉,玉容消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在这时候有了变化。
康熙十七年,夏(四)
对于陶之典,我开始有意的躲避,那个亭子,那个角落,我没再去过。
“灵丫儿,那个西瓜多放点儿,安王府的这帮小主子们看起来都爱吃西瓜。”我坐在榻上,停下手上的绣活,对正在桌子旁边收拾的灵丫儿说。
“知道了,主子,您绣的怎么样了?”灵丫儿指挥四儿把西瓜摆好,转过头问我。
“绣的差不多了。”
“你不是说除了给公主跟郡主绣以外,这些小格格的东西您是一针都不动了吗?”
我翻了她一眼,用嘴把多余的线头咬断,可是咬了半天没咬断,松了口,这才说,“那也就是说说,都是自己的儿女,我也是女儿家过来的,额娘当时要是不给我弄贴身的衣服,我那眼泪估计把娘家大门都给淹了。再说了,”伸手拿过剪刀,嘎蹦把线头剪断,“别说是这些格格,就是塞楞额的媳妇我不也给做了几套吗?”
灵丫儿走过来,把我手上的剪刀接过去,笑着说:“那是,主子以前那可是五指不沾针线的,现在是拿得起放得下。”
“笑我是吧,你不也一样,偷偷的给儿媳妇绣东西,以为我没看见?”斜着眼瞥了她一眼。
没等我说完她就低着头笑了。
“作父母的不都是这样吗。哎,灵丫儿,有没有人说你笑起来好看?”看着灵丫儿笑,我就想到陶之典那天说的那句话,“您知不知道,您笑起来很漂亮?”是女人大都是喜欢别人夸的,我也是,陶之典的话吓得我是不敢再去见他,这多少有点儿避嫌的意思,但是他的话我倒是一字不落的记下了。
灵丫儿好像是没听清,诧异的看着我,重复了一句,“主子,您说什么?”
“我说有没有人说过你笑起来好看?”
“这,”灵丫儿往旁边看看,四儿只是低着头摆放碗筷,没往我们这边看,可是灵丫儿还是不好意思,她一不好意思,那脸就红了。
“又没外人。你们拉瓦纳就没说过?”我知道自己此时此刻的表情有点儿像外面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
“说过,他还说我长的好看。”灵丫儿很小声的说完,没等我继续问,自己就走到桌子跟前,跟四儿一块儿摆碗筷,脸上的红晕还没下去。
我笑了一下,岳乐可从来没说过。
低下头继续手上的活。
就在我等孩子们一块儿来消暑的时候,岳乐的信来了,信上除了问家里的情况,没写别的,只是在最底下写了一首词,岳乐什么时候还开始玩起这个了?我摇摇头,笑了笑,看下去。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这是岳乐第一回在家书后面写词,不是他自己填的,是前人的词。看前面时,我的心被岳乐词中有意无意的这种凄凉惊了一下,南方的仗是越打越顺,可是岳乐的心怎么就成了这样,是思家还是前方有事?但是最后那几句,还是看的我心暖了一下,奇了怪了,这没人夸就是没人夸,这一被人夸就来了两个,还佳人呢,正自己在这儿琢磨味儿呢,孩子们呼啦啦的进来全了,我赶紧把信收了起来。
嫁出去的令瑞、令晴跟静睿不算,剩下的,除了姗姗来迟的塞楞额,其余的,都是一块儿来的,玛尔浑、塞布礼、令雅、令含、经希、蕴端、令钰,一溜溜全涌进来,这孩子一进来,我这屋子就显得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