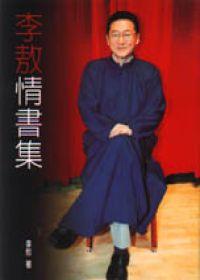清史情书-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嗯了一声,我低着头,看不见他的表情,他顿了一下才说:“今天回来的时候,宫里的梅花也开了。”
“开得好吗?”
“好。”
我把手中的笔在砚台里沾了一下墨,没再画下去,只是看着画,接下来的一笔我有点儿不知道往哪儿落了。
“怎么不画了?”
“您说这儿要不要画满呢?”
“哪儿?”
“就这儿。”我用笔指指。
他转过来,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下,然后把我手中的笔拿过来,弯着腰,自己在上面添了一笔。
“怎么样?”他直起身,转过脸,看着我。
“不错,王爷旁观者清。”我从他手里把笔接过来, 他往旁边让让。
岳乐添的这一笔确实不错,满与不满之间,往往就在于一笔,白漏的多了,画就空了,填满了,画就少了意境。
“王爷有事儿吗?”我继续画我的,他就站在我身后看着,可是我知道他肯定有事,没事儿的话,干嘛在我这边和我说了这么多废话,有女人等着他暖被窝呢。
“没事儿。”
“那我就画我的了,您就自便吧。”其实,这是很明显的逐客令。天已经很晚了,我有点儿困了。
“想和你聊聊。”
“今天没太阳吧。”我从笔架上拿起一根细豪,在砚台里裹了一下墨,画了一个蕊。岳乐今天竟然想和我聊聊,太阳没从西边出来吧。
“没有。”
“那您就说吧。我听着。是正事儿的话,我就停下来听您说。”我把笔停住,等着他的话。
“随便聊聊,你画你的。”
我没吭声,继续用细豪画梅蕊,细细的淡淡的一勾,一朵画好的梅花就出来了,看着画,我笑了笑。
岳乐过了好半天,才在我身后说:“知道刘备临死前托孤的事儿吗?”
刘备托孤?我手中的笔不留痕迹的停了一下。
“知道,王爷怎么会问这个?”
“没什么,刘备托孤前曾经说诸葛亮可自代为成都之主,你觉得会是真的吗?”
“王爷觉得呢?”我没正面回答,反问了一句。
“不知道。”
“王爷也是这么多年在朝堂上走动的人,这件事的真假,王爷应该清楚。”
他从我身后走到里屋的罗汉榻上,靠着软枕,看着我。
“我就想听你说说。”
“其实,历朝历代上演的这种托孤的戏,您看的还少吗?”我抬起头,斜着眼睛看着他,他没吭气,把靴子脱了,盘着腿坐到罗汉榻上,很明显是准备听我说的样子。
我笑笑,低着头,用笔画梅花的枝,梅花好画,它的风骨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枝干上,这也就是很多人画梅时,在花上轻描淡写,但在枝干上却是下足功夫的原因。花虽好,只是仍脱不了花的媚态,若论风骨还是要看枝干的,这一点其实就像女人,外表虽然可能都是千娇百媚,但是内里各有不同。
把剩下的几笔画完之后,我才把笔放在笔托上,端起高几上还有点儿温的茶,坐到了岳乐的对面。
给他倒了一杯,给我也倒了一杯。
他没喝,只是看着我喝。
其实我心里在想着一件事,这样的情景,四年没有过了,其实自从去年七月额娘找岳乐谈过之后,虽不明显,但我感觉的到,岳乐对我说话的时候,已经少了几分刻薄,可是这样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话,还真是第一次。
我把茶杯放下,用帕子擦了嘴,这才开口说话。
“历朝历代,这种事不少,可是刘备的托孤却颇有点儿意思,有人说,此事只有刘备做得出,诸葛亮承的起。话说的没错,可是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自古以来,皇权和相权就不可能真正达到契合,总是此消彼长,因为没有一个皇帝是真正可以放下手中的权的,就是后主,难道就真的对诸葛亮的专权毫无怨言,显然不是,要不然就不会在诸葛亮死后二十多年才建祠,对诸葛瞻,也是一点儿实权都不给,这不很明显吗?”
“那你觉得刘备说诸葛亮可自代成都之主的话,会是真心的吗?”
“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说真的人认为刘备一向以匡扶汉室为己任,他知道自己的儿子难以担当起兴复汉室的重任,所以才要诸葛亮为成都之主,说假的人以为,这是害怕诸葛亮事后权势过大的探测之语,有人甚至说刘备说这话的时候,在背后就立了刀斧手,只要诸葛亮稍微流露出一点儿为主的意思,刘备就会以窥觑皇权的罪名把他杀了,所以诸葛亮才会在说完忠心不二后,背上出了一层冷汗。”
岳乐没说话,只是低下头,用手指在腿上轻轻敲打着。
过了一杯茶的时间,岳乐才抬起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问我:“那你认为这是探测之语了?”
“也不完全是,但是任何皇权的交替为什么总是会死人,这就是因为背后牵扯了太多的利益,纵使皇上有意传位给谁,那他背后的那些人会同意吗?一个皇位的传承,其实是很多利益的相互交锋与妥协。”
我停了一下,才接着说:“王爷应该比我更明白这一点,王爷应该记得当今圣上继承大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
当年太宗皇帝驾崩,两黄旗要立太宗长子肃武亲王豪格,可是两白旗却支持多尔衮,最后,各派争执不下的时候,才决定两人都不立,转而立太宗第九子,就是当今圣上。可以说,皇上的登基其实就是各派势力利益的交锋下妥协的结果。
岳乐听完这句话,忽然笑了,整个人看上去轻松了很多,他把茶杯放到炕几上,往后一靠,说:“没错,有人不会同意的。”
“您说什么?”我怎么总觉得岳乐今天说的这些话好像是有所指,但是又说不上来到底所指何事。
“没什么。哦。对了,你的梅花画好了吗?”
“好了。”
“那我给你题个款。”没等我回答,他就从榻上下来,汲着鞋走到书桌前,拿起笔,就往上写了字。
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用笔在画的右上方唰唰写了几句。
“怎么样?”
他往旁边让让,我往前凑过去,他上面写的是两句诗。
“兰为王者香,梅占百花魁”
“王爷字写得好,题也题的好。”我一边说,一边把笔放在水里涮涮。涮完笔,我把东西收拾好,转过身,看着他。
“王爷,天也快亮了,我要眯瞪一会儿。”
“那你就睡吧。”
我往里屋走了几步,转过身,对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过年的时候,给他们一人一个小线包,里面放了三个银锭子,这笔帐可不是府里的。还有,您要是出门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把门带上,外头还下着呢。”
他只是站在书桌后面笑了笑。
我也是在第二天才知道岳乐为什么那天晚上会说那些传位之类的话,因为就在正月初四,皇上竟然要把皇位传给岳乐。
很多年之后,回过头,看看这件事,皇上对于岳乐,就像萧何之于韩信。岳乐因为皇上,而有了前半生的荣耀,可也是因为皇上,他的后半生过的则颇为沉寂。这大概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顺治十八年,初(三)
岳乐那天没离开,我是在第二天早上被门外的敲门声吵醒的时候,才发现,他在罗汉榻上睡着,没盖被子,就是把炕桌往里掀了掀,侧身在外首睡着。
“咚咚咚。”外面的敲门声更响了,岳乐也被吵醒了,揉着眼睛,往起挪挪身子,看了一眼外面。再看看我,然后才从榻上下来,出了里间,把门打开。
在他去开门的时候,我也把外衣披上,准备下床,还没穿上鞋,就听见一个嫩嫩的声音,“阿玛”,是令瑞。
我穿上鞋,走到门口,岳乐已经把令瑞抱在怀里,她见我,呵呵的笑开了,“额娘。”
我用手拍拍她的脸蛋儿,“冷吗?”
“不冷,额娘给我穿了好多,说是今天早上让阿玛陪我堆雪人。”
看来,岳乐昨天晚上回来的事儿,兰尔泰已经知道了,怪不得人都说,大家庭里才没有真正的秘密,那也就是说,昨天晚上人人都知道岳乐昨天晚上在我房里歇着了。
岳乐刚说了个好字,兰尔泰就从西边匆匆地走过来, 给我和岳乐见过礼,她从岳乐手里接过令瑞,放到地上,弯下腰,在令瑞小屁股上打了一下。
“令瑞,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打扰阿玛和额娘呢?越来越没规矩了!”
令瑞没吭气,只是低着头,在她的腿上蹭了蹭。
兰尔泰没理她,站起身,不好意思的对我说:“这么一大清早就打扰了福晋的清梦,是兰尔泰教女无方,以后不会了。”
“没事儿。”我把外面穿的披风裹了裹,雪已经下的小了,但是还有风。
“冷的话,就进去吧。”岳乐注意到我的动作,对我说。
我看着他笑笑,说:“侧福晋不是让王爷陪令瑞堆雪人吗?”
“是啊,今天阿玛没事,就陪我们令瑞堆雪人,好不好?”岳乐一边说,一边走到令瑞面前,蹲下身,拉着令瑞的手。
“王爷今天不用进宫吗?”兰尔泰拉着令瑞的另一只手,低下头,看着岳乐问。
“不用。”
“那就好,要不然我就对令瑞食言了。”
岳乐的额头挨着令瑞的额头说:“当然不会了,令瑞,阿玛今天就陪你玩一天,还有静睿,你去把她也叫上,好不好?”
“好。”
岳乐对孩子永远是个慈父,不论是冰月,还是令瑞,抑或是其他的孩子,他都爱。尤其是女孩儿,这一点可能和他阿玛很像,老福晋给我说的时候,提到的老郡王,就是一个对孩子,好到极致的父亲。看着岳乐拉着令瑞的手,和令瑞额头对额头抵羊的样子,我忽然想到了那个失去的孩子,如果那个孩子没掉,今年已经六岁了,不知道岳乐是不是也一样疼他?只可惜,永远没了,他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红色的血中浸泡的白色未成形的胎儿,永远都不会长大,想到这儿,我就没有兴趣再看岳乐和令瑞还有兰尔泰的天伦之乐了。
我先是对令瑞说:“令瑞,你和阿玛还有你额娘一块儿玩吧,额娘还没睡够,还得睡会儿。好不好?”
“好。”
“真乖。”我对着令瑞很灿烂的笑了一下,可是对着岳乐的时候,我的脸上就已经恢复了平静。
“王爷,我还没梳理,先进房了,昨天晚上和王爷在一起,还真的有点儿累了,您有事就让灵丫儿叫我。”没等他说话,我一转身进了房,哐一声把门关上了。
“王爷,您昨天晚上和福晋,累着了?”屋外,兰尔泰很小心的问到。
没听见岳乐的回答,只是听见令瑞兴奋的叫喊声:“哦,玩雪了。”
我靠在门上,哭了,为了那个连这个世界都没有看一眼的孩子。
那天吃中饭的时候,灵丫儿一边布菜,一边说:“福晋,今天院子里忽然多出来几个雪人,挺好玩的。”
“是吗?外面有雪,你身子不方便,这两天也就别过来了,有苹喜就行,我一个人,用不着那么多人。”
“那您是不是就准备趁这个机会不要我了?”灵丫儿开玩笑地说,我把头从《史记》中抬起来,笑了。
“是啊,不要你了,你有你们家拉瓦纳要就行了。”
她把米饭往我跟前一放,“我要他能干嘛?”
“没他,你的这个能自己跑出来?”我用手指指她的肚子。
“您说什么呢?”她不好意思的往外屋看看,苹喜在那儿收拾桌子。
我吭的一声笑了出来,还不好意思呢,不过也是,苹喜还没嫁人呢,这种话是该少说。
笑完之后,我才放下书,拿起筷子准备吃饭。
“主子,您才说到拉瓦纳,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是他昨天晚上回来给我说的。”
“什么事儿?”我夹了一口炒鸡子儿,放到嘴里,看着她。
灵丫儿把声音压了压,往外屋看了看,说:“拉瓦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