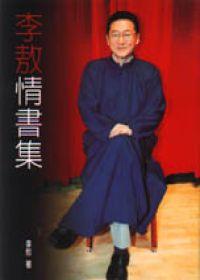清史情书-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这个男人,我永远都不会懂。
我曲了膝,行了礼,转身就走,临出门的时候,我转过身,看着岳乐的眼睛,说:“王爷,我们打了三年的冷战,您赢了,三年前,我没了男人,三年后我没了女儿,一个女人的天,没了。”
刚跨过门槛,我的眼泪唰的流了出来,摇着嘴唇,强迫自己不在岳乐面前发出声音。这个男人,已经不值得我在在他面前流泪。我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的哭一场,可是出了内厅,我突然发现偌大的府里竟然已经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处。房间不能回,冰月在那儿,其他的地方也不能去,到处都是岳乐的莺莺燕燕,我自嘲的笑笑,原来这府里真的就没有我的地方,连哭都已经找不到地方了。
我就茫然的往前走,眼泪就在脸上肆意的流着,我没去擦它们,越擦只能越多,由它们去吧。
我在花园的流觞亭里坐下,这一坐就坐了一整天,眼泪早就流光,我目光呆滞的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儿的斜下去,直到天黑,灵丫儿来找我。
“福晋,您怎么在这儿呀,找您半天了。”
“有事儿吗?”我呆呆的靠着亭子的柱子坐着。
“二格格今天下午去找您,到现在都没回来。”
“你说什么?”我猛地转过头,把灵丫儿的肩膀扯住。二格格这三个字让我清醒了过来。
“今天下午,格格睡起来,看您还没回来,非得要去找您,我说,您有话跟王爷说,可她就是不听,怎么拦都拦不住。等奴才跑出去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
我站了起来,疯了一样往园外跑,冰月,你怎么会不见呢?额娘和你在一起已经没几天了,你怎么还乱跑呢?
从园子到内院要经过书房,于是我听到了冰月的声音。
“阿玛,我不要进宫,我不要进宫当什么公主,我在安王府就是格格,我有吃有穿,有阿玛还有额娘,我哪儿都不去。”
“听话,进宫说明皇上疼咱们冰月,而且冰月进宫之后也有阿玛也有额娘啊。皇上不就是冰月的阿玛,皇贵妃不就是冰月的额娘吗?”
皇贵妃?站在窗外的我一下子逮着了岳乐说的这三个字,皇贵妃是冰月的额娘?
为什么我总是和这个女人扯不清?我统共只见过这位宠妃三面,甚至连单独的话都没有说过,可是上天却总是将我和她联系到一起。顺治十一年,我们几乎同时被指婚,顺治十三年,为了她,我与岳乐闹翻,顺治十六年,她把冰月从我身边带走,她成了冰月的额娘。不由得我不自己取笑,敢情儿我和这位娘娘真有缘分。
“皇贵妃不是我的额娘,是别人的额娘。”
“皇贵妃的儿子死了,皇贵妃就想让冰月进宫,当自己的女儿,她会对冰月好的。”
原来,这位皇贵妃丧子之痛到现在还没缓过来,于是,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就掉到了安亲王府的头上。她的丧子之痛缓不过来,可是她还有一个疼她的皇上,我有什么,失去冰月,我什么都没有了,就像我对岳乐说的那样,三年前,我没了男人,三年后我没了女儿,一个女人的天,没了。是,我还有安王福晋这个位子,可这个位子,换了谁谁都能坐,谁都坐的比我好,最起码,她们会笼络自己的男人,她们有自己的儿女。
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又流了下来。我用手把嘴捂住,拼命的让自己忍住。
“那皇贵妃会教冰月读书吗?她比额娘知道的还多吗?”
岳乐停了一下,才说:“皇贵妃的额娘是汉人,皇贵妃知道的东西肯定不少。她会教冰月的。”
“冰月不去,冰月去了,就没有人晚上给额娘擦眼泪了。”冰月在里面哭了起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到书房门口,啪一声,书房门被我推开。
“额娘!”冰月见到是我,一下就扑了过来。
我蹲下身,用手帕给冰月把眼泪擦掉,然后把帕子掖好。眼睛平视着冰月,她的眼里全是泪水,我笑笑。我不能在孩子面前哭,我知道有些事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当你不能去改变时,接受是唯一的法子。
“冰月,别哭了,就要进宫当公主了,成大人了。”
“冰月不想进宫,冰月想和阿玛额娘在一块儿,还有静睿。”
“冰月,你姓什么?”
她抽噎了一下,红着眼睛说:“冰月姓爱新觉罗。”
“那皇上呢?”
“也姓爱新觉罗。”
“这就是说,你和皇上是亲戚,你是宗室。冰月,额娘今天说的话你要记住,宗室,虽然身份光鲜,但是生由不得我们,死由不得我们,命也由不得我们。当你不能改变命的时候,那就试着去接受它,让自己在别人规定的命中活出精彩,活出自己的人生。命由不得我们,但是怎样去过,这,是我们自己的。”
冰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趴到我的肩膀上,小肩膀一抽一抽的。我把她抱起,往书房外走,没再看岳乐。
那天晚上,冰月在我的怀里哭着睡去,我抱着她,没几天了,抱着她的日子没几天了,这么乖的孩子,以后再没有人在晚上给我擦眼泪了。我用嘴咬着自己的手指,这时,只有肉体的痛才能减轻心里的伤。
在我睡着的时候,我梦见了岳乐,他没有瞪我,没有朝我发火,也没有平常的冷嘲热讽,而是很温柔的在我咬得满是疮痍的手指上抹上了凉药,凉凉的,很舒服,但那只是一个梦,虽然第二天我在手指上闻到了凉膏的气味,但是灵丫儿说,那是她帮我涂的。
一个月后,论故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前罪,削巽亲王、端重亲王爵,降其子为多罗贝勒。敬谨亲王独免。
顺治十七年,夏(上)
顺治十七年
董鄂妃逝。
冰月进宫已经半年多了,我没有进宫,即使是在皇太后万寿节的时候,我也找个借口推掉了,我不愿意看到冰月在皇贵妃的怀里叫额娘的样子,不看,或许我还会认为我是冰月的额娘,看了,我就永远的失去了冰月。
我和岳乐的生活继续,他照样让他的女人怀孕,他的孩子照样一个一个出生,今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在跨院里还有一个即将生产的庶福晋张氏,算日子大概也就是在八月初,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孩子出世了。
我照样在房间里写写画画,只不过少了冰月,整个房间里就显得空荡荡的,用灵丫儿的话说就是,有时候冷的跟冰窖一样,其实这句话说的没错,我现在不就是被王爷打进冷宫的女人吗?只不过,头顶上仍然顶着嫡福晋的帽子,这顶帽子又让我不得不四处走动,遇喜就笑,遇悲就哭。前两天,简亲王济度薨,我在济度的灵前和一群女人们痛哭流涕,哭得眼睛都红了,但是谁都明白,这不过是逢场作戏。
可是人生本来就如戏,我和岳乐从成亲走到今天,这场戏演的轰轰烈烈,却又冷冷清清,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从我穿上凤冠霞帔的一刻,这出戏就开唱了,只不过一开始岳乐就对我有抵触,他根本没有试着去爱我,只有我傻傻的将自己沉了进去,不甘心只做福晋,还想做他的女人,他爱的女人,可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弦索胡琴不能免俗的是死别生离,这出戏演到最后只能是凄凄惨惨戚戚。
大哥在快过年的时候没了,大哥不仅是长子,还是嫡长子,他的死对这个家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额娘整整一个月没有缓过来,大嫂也病下了,整个索家乱七八糟,我在索家呆了两天,每天就只见阿玛一个人弯着腰走来走去,身后再也没有大哥的身影,阿玛一个人的身影就这样被太阳拉的细长细长的。
今年上半年,整个清王朝似乎也灾害连连,天灾,人祸,战乱,皇上甚至在三月间下了罪己诏,可是皇上毕竟只是天子,他还管不了天的事。管不了天,他也管不了病的事,董鄂妃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听说这几天病是越发的重了,可是皇上在面对自己最亲爱的女人的时候,即使贵为天子,他也照样束手无策,生老病死不是由天子管的,而是由地君管的,皇上,只能管天下地上的事,其余的,他和我一样,只能听天由命了。
前朝后朝都有事,所以今年岳乐就更忙了,不要说我,就是侧福晋乌亮海济尔莫特氏也在我跟前说,很长时间没见王爷了,几个孩子都不会叫阿玛了,我听了也只是淡淡的一笑,作为福晋,我可以让岳乐雨露均沾一点儿,但是当我都看不见他的时候,我这话就是想说也没的人说。
今天可算逮着空了,岳乐今天没进宫,早上派人过来说,今天一块儿去三爷府看看老福晋。自从去年年底,皇上削去端重亲王爵,夺谥之后,端重王府在我们的口中就变成了三爷府,毕竟端重亲王这个名号从此以后就没有了。再称呼端重王府就不太好了。
本以为儿子死后被削爵夺谥,老福晋的身子受不了,可没想到,她的身子骨倒反而是越来越精神了。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种反常其实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只不过,当时,我们都在为老福晋的身体好转而高兴,还准备为她过六十大寿,最终这个寿没过成。
“王爷?”我在车上坐着的时候,靠着车厢,看着坐在我旁边闭目养神的岳乐,又瘦了,真不清楚,这个男人怎么瘦的这么快,原先还有点肉的脸,现在已是棱骨分明,下巴上也开始出现了胡茬,黑压压的一片,我们这位平常很注重仪表,注重门面的儒雅王爷怎么成了这样一副模样,一会儿让老福晋看见,怕是又没什么好脸色看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岳乐消瘦的脸庞,我竟然很有一种上前摸摸的感觉,手就那么贱的伸了出去,和我刚成亲的时候想要摸他的鼻子一样,被他拦住了。
“王爷,您醒了?”我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回。
“有人想要要我的脑袋,我能不醒吗?”说也奇怪,自从冰月进宫后,岳乐对我说话的语气就有了一些变化,我们两个以前说话的方式常常是他的冷嘲热讽,我的冷冷淡淡。可是现在,我很少从他的嘴里听到那些带刺的话语,仔细算算,岳乐也是三十五的人了,许是年龄大了,话语也平和了很多,就像他的眼神,以前是平静如水,现在则是沧桑如茶。
我笑了笑,说:“我还指望王爷的俸银养活呢,王爷没了脑袋,我吃西北风去呀。”
“东南风吃得吃不得?”
我们两个人同时哄然大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惬意的时候了,惬意的让我觉得就像是在梦中,就像是那天晚上,岳乐温柔的在梦中的一样。原来我们也有这样的时候。
进了三爷府,本来要和岳乐一起像老福晋请安的我却被挡在了门外,老福晋传话说,她要和岳乐说几句话。
三嫂没在家,她和奇克新的福晋一起去庙里求平安去了,听说,奇克新自从被降为贝勒后,不是整天喝酒,就是挟妓私游,三嫂已经派人请过岳乐几次了,可是过后依旧。没有人接待,我就只能在府里乱转。转到一处房间的时候,我听到里面传来哭声,是一个男人很压抑的哭声,想哭可是却不敢哭的声音,虽然只是几声轻啜,但是我还是听出来了,是奇克新。
虽然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我还是决定走开,一个男人就像是一匹狼,他受伤的时候最好让他一个人独自把伤口舔干净。
顺治十七年,夏(二)
可就在我刚准备挪开脚步的时候,我听到奇克新说了一句四婶,我登时站在原地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以为他发现了我在房门外,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老老实实的把门推开,进去。
刚进去,一个花瓶就哗的砸过来,“出去,滚!谁让你进来的!狗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