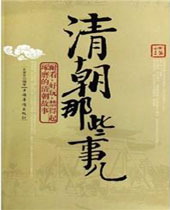那些花儿,那些青春-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脱掉外套,在舞池中央扭了几下,突然有种伤筋断骨的痛。有个陌生男人蹭到我身后来,搂住我的腰,身体在我后背上摩挲,我转过身去,看到一张陌生的男人的脸,又远又近,像一场迷梦。他只是个陌生人而已,我并不认识他,兴许我在茫茫人海中和他擦肩而过无数次了,兴许我从来就没遇见过他。
我突然有种冲动,想跟他接吻的冲动。
音乐声停了的时候,我和朝晖、冯桥还在,我们喝得晕晕忽忽,忘了所以。朝晖都忘记跟我分手了,跟我说老婆今天晚上回去我要吐了你就甭管我了,你自己好好睡吧,你这几天要好好照顾自己。冯桥也晕了,跟朝晖说哥们一回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课堂上见!
我的眼泪如泉而涌,我放声大哭起来。我们曾经是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们一起开心一起伤心过,今天我们一起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我们勾肩搭背的在大街上晃晃悠悠地走着,冬天的刺骨寒风刮在脸上,我们忘记了痛。走回学校里,坐在体育馆看台的台阶上,三只烟的火星同时亮起来,像三朵美丽的花。
我们哭了。抱在一起哭了。
晓晓和刘西的家装修得真漂亮,一进去就觉得亮堂堂的,跟五星级酒店的大厅似的。我说晓晓你小丫头不错嘛,前阵子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会儿就奔小康了?
晓晓说我的亲姐姐,您就甭笑话我了,像我们这样的善良小老百姓,这样活着也挺好的。
她的一句话仿佛击中了我内心里面那根最脆弱的神经,原本每一个女人有着一个宁静的梦,想做一个快乐的家庭女人,我也不例外。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觉得这个梦不适合我了,我一时之间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比如我最近就常常发呆,我站在公司的窗口发呆,在公共汽车上的时候也发呆,就连走路的时候也觉得大脑是空空的。
除此以外我还还觉得最近自己倒霉到家了,我自己的脸上都快掉霉灰了,去美容院洗脸的时候美容小姐问我:大姐,敢情你会保养吧,这么年轻?
我说你猜一下我多少岁了?
美容小姐笑呵呵的:你嘛,最多孩子上小学的样子,不像我,都三十六七了,孩子都上中学了。
我心想,靠,我有这么老了吗?孩子都上小学了?
上班的时候把这事跟肖伟说了,他笑得快倒地上了。我挥舞着胳膊,十分愤怒,我说你相信吗?我最近霉死了。我在大街上走着走着撞一木桩子上了,结果我还被静电打了一下。
昨天下班的时候回家,公共汽车上挤得都快要爆炸了。我死死抓住挂钩,左手就垂在身体旁边,不停有人把我挤得东倒西歪的。车行了一段我突然觉得左手背痒痒的,像有东西在上面磨蹭。于是就在我低头的那一瞬间,看见有个极端龌龊的家伙裤链拉开,他的那玩意儿正在我手背上摩挲,兴奋得难以自抑。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立刻收了回去,脸色变得煞白,眼神慌张。奇怪的是我并没有立刻发火,我只是咬着牙齿说了句傻逼
()
我想要是在以前,最起码在三个月前,那我肯定二话没说抡起胳膊都给丫一大耳光,打完了再笑着问他还需要么?
可能我变了,最近我更乐意于去学习做一个淑女。原本我的骨子里就不是淑女的,只是最近我十分懒,我懒的就算看见了杀人放火强Jian,也不会叫一声,所以看起来我是文静了很多。我这种生活的状态让人看起来是苍白和惨淡,而我自己觉得,那叫灰心。
我看着朝晖从成都离开,我多余的一句话也不想说,我就跟他拥抱了一会儿。我看着冯桥从成都离开,我就说了句哥们保重,少喝点酒。
我问晓晓,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站在一片大海边,闭上眼睛,听着潮水的声音,迎面是阵阵温柔的海风,你把双臂伸展开来,此时此刻,你会是什么感觉?
晓晓想了一会儿,说我的妈呀,那我肯定会哭起来。面前除了一片大海,什么也没有,还是黄昏的时候,天也是黑的,海也是黑的,我不哭才怪!
我笑着说我的新娘子啊,都跟我混这么些年了,还这么胆小。要我的话肯定会保持那个姿势半小时,然后心里不停的企求:潮水啊,来吧,把我吞噬了吧!
我很少说话,但是我渴望有一场翻天覆地的灾难降临。也就是说我想重生一次,想在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一切从零开始。
从晓晓家出来的时候,她在我的耳朵边悄悄说,一个月前她怀孕了,所以才这么着急着结婚。我说看不出来嘛,你小样的也学会了先上车后补票?
风呼呼的在耳边吹着,耳朵硬得象两片铁锁儿,轻轻一碰就觉得疼。我心想成都怎么也会冷成这样,跟北京似的。
看到晓晓一脸幸福的模样,竟然有几分嫉妒她。原本我也可以是一个快乐的女子,只是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人生千万不能想,一想准会流泪。
在肖伟跟我求婚的时候,我听到身边无数个声音在喊:答应他吧答应他吧!
可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单膝在我面前跪下,我第一个感觉不是感动也不是幸福,而是冲动,我想把他抱起来的冲动。可能是我已经习惯了过去的生活,每次朝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在我面前跪下,我都会把他抱起来,然后告诉他没事了没事了我已经原谅你了!
奇怪的是我总是原谅他,他也总在一错再错直到最后错得一发不可收拾,而我不想再原谅他。我想我可能这辈子也没法走上红地毯了,是从我内心散发出来的一种本能的感觉:我做不到!
第四部分 生活了四年的城市 第47节 失去了知觉
春节临近,公司琐事颇多,让人心烦。
我妈突然打电话过来,就在昨天半夜里,她的语气有些慌张,口齿也不清楚,我听了大半天才稍微明白一点,就是我妈让我去买一份北京出的报纸来看看,上面有与我有关的重大新闻。
挂了电话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半夜里没有人会卖报纸,所以我特别慌张和郁闷。我坐在沙发上光着脚丫子抽了半盒七星,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天都蒙蒙亮了,整间屋子被我弄得跟地狱似的,烟雾弥漫。我连忙把窗户打开,一口风灌了进来,我爬进被窝里,把头埋着,一会儿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我赶紧穿鞋随便披了件衣服跑到楼下马路边的报刊亭,买了一份《北京青年报》,卖报纸的那小伙子说我运气还比较好,要在其他亭子里面肯定很难买到北京出的报纸,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便拿着报纸赶紧往家跑。
〃都市白领丽人罗与华女士香消玉损,前夫悲痛过度住进医院,身后上千万家产及其在XX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由其子继承,据可靠消息其子于葬礼当天离开了北京,且目前不知去向……〃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立马便失去了知觉。
我不知道沉默了多久才苏醒过来,我拿着电话的双手一直在发抖,我喃喃地对肖伟说:给我定张机票吧,多晚都行,但今天一定要赶回北京。
肖伟问出什么事了?
我说甭问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了。
推开门我妈便上来抱住我,我眼泪排山倒海就来了,我说妈,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
我妈说孩子,我知道你难过啊,我也很难过。报上说她喝醉了,把车开上了高架桥,撞栏杆上了……
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想起冯桥他妈当初打我的那一耳光,那样火辣的感觉这会儿好象还留在脸上,我还觉得脸上如刺痛班难受。我今天在成都机场的侯机厅里的时候,不停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手指甲,我回到北京我才发现,十个指头的手指甲都快我啃得乱七八糟,粗细不平了。
我开着我爸的破桑塔纳在二还上转了一圈,最后又把车开上了三环,转完三环的时候,我趴在方向盘上大哭起来了,我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伤心成这样,应该伤心的是冯桥啊,可我为什么却是如此的悲痛欲绝。
我实在太年轻了,我年轻得经不起任何一丁点儿的打击。才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眼睁睁看着身边熟悉的两个人就这样活生生的没了,我能不难过么我?我妈打电话了,问我在哪儿,我说我不知道,我妈急得都快疯了,说你下车问问你到底在那儿?我说不用问了,我在樱花西街。我妈咆哮着说你疯了啊,你跑那么远干嘛?我说不知道,我停下来的时候就发现在这里了。我妈说你赶紧回来,你再不回来我立马跳楼。我哭着说妈,你甭吓我,我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我在冯桥他们家门口的马路边站了好久,就这样矗立在寒风中,我冻得直哆嗦。那幢昔日神采奕奕的别墅现在灰暗得像面潮湿的黄土墙。冯桥的手机停了,连我都没办法联系到他了,何况别人?
保安看到我就朝我直摇头,唉声叹气的,一句整话都说不清楚,就听他吱吱唔唔的老说〃他们家,唉〃
()好看的txt电子书
〃唉他们家〃。
他气叹得比我还多。我把手揣在大衣的包里,把帽子拉来包住头,我蹲在地上大声哭泣了起来,他一边扶我起来一边说你甭这样啊甭这样啊,你这是吓我呢!
我给朝晖打电话,我说朝晖,给我讲个笑话吧,我又不开心了。
朝晖的声音沙哑,喉咙像堵着口浓痰。
新年的钟声是和爸妈一起听到的。
一觉醒来,看到窗外光线明亮得刺眼,我连忙穿衣下床,随便洗了把脸,丁冬丁冬跑到楼下,刚走到赵姨家门口,正准备伸出手去按门铃,王蕾就已经穿得整整齐齐的站我面前了,看见我,就说了一字儿:走!
我们俩先在楼梯口坐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堆雪人。王蕾的头发剪短了,我还记得以前每次堆雪人的时候她的头发都会斜斜地从肩头滑下,看着她那张清秀的脸,觉得很美丽。而如今我的头发长长了,我还得像她当年一样,不时拿手背把头发往后揽。
我问王蕾:你现在觉得开心了吗?
王蕾点点头说很开心,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以前总觉得像在为别人活一样。
哎真没白白教育你。
得了,听你妈说你和朝晖的这条路走得特不顺,弯弯拐拐的。
是啊,都成山路十八弯了,比鹅肠子还曲折。
到头了没有?
不知道。觉得像明白了很多。
不知不觉,终于堆好了一个比我们俩合起来还大的雪人。我们俩互相看着傻笑了会儿,于是坐到楼梯口,看着雪人。王蕾从羽绒服地掏出一盒烟来,问我:抽吗?
我点点头,接过一只,王蕾拿火机给我点上,几秒种后白色的烟雾就慢慢升起,和冬天的雪色混在了一起,因为太柔和,所以没有人会在意它。我看王蕾抽烟的动作,很是娴熟,娴熟得像我没法相信她就是我们家楼下弹着《秋日的丝语》的王蕾。
我们原来在对方心目中的样子,已经破裂,不复存在了,一切仿佛已经万劫不复。有时候多想时光能够倒回,或者能在某一个美丽的瞬间定格。
多年以后我明白了,是我太傻了。也就是说,我长大了。
我问王蕾:想弹钢琴吗?
她眼睛迅速地向楼上看了一眼,说:走!
于是我们俩开始上楼。我说想弹《秋日的丝语》还是《命运》,王蕾斩钉截铁地回答:都弹!
还真干脆,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