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之晨-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付展风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道:“展风对名利向来不曾在意。不然以在下的身手,武状元也当得了。”
“这话也有些道理,那我就更不懂了。”
“其实也没什么,不过是遵从师命罢了。”
提到朱景溟,上官若愚便气不打一处来:“我瞧你也不算个蠢货,为何要这么听你师父的话?”
“若没有师父,展风便什么都不是,甚至连活不活得到今日也未可知。师父对我恩重如山,我奉他为尊,有何不对?”
“恩重如山,便能连是非都不辨了么?”
“小于姑娘是指南靖王爷的事么?”
“哼,你倒有脸提!”
“姑娘聪明灵慧,却不知有没有想过,以师父的本事、当年在江湖中的威望,为何进入陆府十二年,却仍只是个武师?他若一心向往荣华富贵,又怎会甘心守在尚书府这么多年?”
上官若愚一怔,这一节她也不是不曾想过,但内心总是排斥一切能为朱景溟辩驳的理由,因此每每想到这里,便要硬生生地勒住。此时仍不禁嘴硬:“缘由如何,与我无关。我只知道,他出卖我师父,害我师父葬生天牢却是事实。我师父与我也是恩同再造,无论如何,师仇不可不报。”
付展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展风说这些,不是奢望小于姑娘尽弃前嫌,只望姑娘明白,我师父当年这样做,亦是有他苦衷的。”
“好,我如今明白了。那今后可以大大方方地报仇了么?”
付展风微微笑道:“姑娘请便。”
上官若愚一时气结,头靠在墙上默然不语,两人一时无言。
过了一会儿,忽听陆陵一声惊叫,接着身子直弹了起来:“救我!”
付展风急忙伸手拉住他,按住涌泉穴,助他缓缓定神。陆陵如梦初醒,尚自浑浑噩噩,抬头四望了一下,说道:“天怎么黑了?”
待他静下神来,付展风才将适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陆陵听完后,惊叫道:“那现在怎么办?难道要在这儿关一辈子?”
上官若愚在一旁幽幽答道:“一辈子是不会的,最多五天。”
陆陵心中一喜,问她:“你有法子五天后就能出去,是不是?”
“我是说,人若没水喝,顶多撑个五天。”
陆陵听她又在戏弄自己,却顾不上生气,陪笑道:“我知道你又是在吓我。你鬼主意多,这一路过来都是听你的。你告诉我,咱们怎么才能出去?”
“我哪里是在吓你。若能出去,我现在又岂会干坐在这儿。”
陆陵一跃而起,大叫道:“我不信!我不信!这密室之中定有机关!你们快给我找,不许坐着!听见没有!”
付展风劝道:“少爷稍安勿躁。”
陆陵道:“你给我起来找去!听见没!”
上官若愚道:“这暗室本就是个陷阱,关人用的。若换了是你,会不会蠢到在里面再按个机关,让敌人自己找到,得以脱身出来?”
几句话,直说得陆陵心如死灰,绝望道:“如此说来,我们这回是要死在这里了?”
上官若愚抬头望着那封死的暗板,口中喃喃着:“那就要看天意了……”
39
39、三十九 。。。
漆黑之中不辨时间,只知道陆陵吵闹之后,又坐着哭了一阵,三人的腹中都开始“咕咕”叫起。陆陵饥渴难耐,又手足无措,煞是难熬,上官若愚终于看不下去,伸掌成刀,在他颈后一劈,室中才又复归清静。
付展风没有阻挡,只是伸手接住陆陵的身子,将他扶到墙边躺好。
上官若愚轻揉着额角,说道:“若是他快醒了,记得再补一掌,吵得头都疼了……不知是吃什么长大的,嗓门这样‘清亮’。”
付展风微微一笑,默然不语。
真等这室中寂静无声了,上官若愚却又不觉心慌起来。想那五年她都这样过了,却不料反而是出来之后,变得这般容不得黑暗。
便又忍不住开口说道:“喂……”
付展风应着:“嗯。”
“你别闷着,说说话。”
“小于姑娘不是不爱听人吵闹么?”
“你少爷那岂是‘吵闹’,简直比女人还呱噪了。我都耳鸣了,再不打他,就该失聪啦。”
付展风又是轻声一笑,道:“少爷有时是任性了些。”
“你也当真好欺负,若换了我,这厮的皮都该被我剥掉三层了。”
只听付展风笑道:“那是,姑娘是江湖上闻名的‘皮作师’嘛。”
上官若愚一怔,想起自己吓唬陆陵的那句玩笑,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忽听付展风问道:“姑娘不喜欢暗处?”
上官若愚微微一愣,一时想不出自己有何明显的表现,不料他心细如丝,竟是隐隐察觉到了,当下也不隐瞒,点头应了一声:“嗯,不喜欢。”
付展风静默了片刻,忽然站起身来,移坐到她身旁,笑道:“其实我也不喜欢。可若是有人陪着说话,便感觉好了许多。”
这话读不清用意为何,却正正说进心坎。上官若愚轻叹一声,只听付展风又问道:“小于姑娘可喜欢音律?”
上官若愚不禁暗笑:她让他说说话,他倒真的话不停了。于是答道:“略通一二。”
付展风道:“枯坐无聊,那在下便献丑一曲寥以解闷,如何?”言罢,自腰间取出一管长笛,放在唇边吹奏起来。
他吹的是一首古曲,上官若愚曾在江南的小巷中听人吹过一次。当时只觉得曲调轻幽舒缓,如今在一片漆黑中再次听到,仿佛便闻到了江南五月干净的空气,看到了湿漉漉的青石板和滴着水的灰檐,心中顿时一片安宁。
她赶了一天的路,又忙碌奔波了半晌,大半天未进米水,此时已是累极。听着付展风极尽委婉的笛声,倦意阵阵袭来,眼皮不住打架,却始终不敢阖眼睡去。
付展风见她面有倦意,却着意强撑,轻声叹息了一句,笛声自高折低,渐渐隐去。
上官若愚问道:“为何不吹了?”
付展风道:“再吹下去,只怕姑娘睡意更浓,如此强撑,唯有更加难受。”顿一顿,又道,“小于姑娘不睡,可是放心不下我?”
上官若愚见他识破自己心思,也并不十分在意,淡淡笑道:“我若说已将你当成朋友,你可会相信?”
这话,语调轻佻,显有嘲弄之意,却不料付展风竟正色下来,认认真真地答道:“相信。”
上官若愚不禁望了他一眼,黑暗之中,虽看不清容貌,却仍能感觉到他那一双眸子灼灼地望着自己,忍不住说道:“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付展风道:“只因在下早就将小于姑娘视作朋友了。”
上官若愚不禁冷笑一声,道:“这样便是朋友了?看来你的朋友当真是少得可怜。”
付展风不怒反笑,淡淡答道:“确实是少得可怜。展风活了二十几年,也只得小于姑娘一个朋友而以。”
上官若愚怔了一怔,道:“到底是你做人不好,还是尚书府中没有正常人?”
付展风微笑道:“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也对,似你师父这般的为人,还是不要交朋友的好。免得害人害己!”
“师父为人如何,暂且不论,小于姑娘觉得展风是个什么样的人?”
上官若愚望了他一眼,道:“阴鹜内敛,深不可测。”
付展风哈哈大笑,道:“看样子小于姑娘还在记恨扬州的事。”
“几十条人命,岂是说忘便忘的?”
“不错,那些确也算是无辜之人。但当时姑娘行踪诡秘,来历不明,为了确保少爷安全,展风也只有出此下策。”
上官若愚冷笑道:“好狠的‘下策’!”
“狠是狠了一些,不过却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姑娘适才说我‘深不可测’,实在是太抬举在下了。其实在下做事最是简单不过,只求个‘稳妥直接’罢了。做人如是,做事如是,看人亦是如此。”
上官若愚冷笑道:“我可不是什么‘稳妥直接’的人。”
“姑娘心有百窍,玲珑剔透,对我和少爷亦是不怀好意思……”他轻轻浅浅地说着,仿佛并不在意那最后一句的意味,见上官若愚不答,便接着说道,“但这些不过是粗浅看来。我却觉得姑娘是个简单善良,值得相交的人。”
“噢?”上官若愚有了些兴味,挑眉问道,“所凭为何?”
“就凭我腿伤上绑的衣襟。”
上官若愚这才想起,那日他自残右腿后,血流不止,她扯下他的衣襟为他止血疗伤。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件小事,不想他却一直记在心上。
只听付展风又道:“你我本是敌对,在下昏迷之时,姑娘大可废我武功,毁我经脉,最不济的,也应不理我的腿伤,由它再多失一些血,伤我元气。可是姑娘还是出手相救,可见不论你装得如何凶煞,心却还是软的。这样的人,展风还是头一次碰到,因此早已引以为友。”
其实还有许多话他没有告诉她。他自小为朱景溟收留,学文习武,日夜不辍。朱景溟的武功博大精深,若非极严苛的打下厚实基础,以后难有大成。因此从小到大,受伤已是习以为常。
在尚书府中,他不过是武师的弟子,没有人会在意,师父和师兄、师姐都是习武之人,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更是没人会关心他伤得重不重,痛不痛。尚自年幼之时,他自己去药房找药,有时找不到,便干脆只用布条紧束。第二日稍一用力,便又迸开,如此反复,伤口流脓溃烂,终留创疤的不计其数。
那日腿伤,于他不过是最最寻常之事,醒来却发现伤口已被整整齐齐地包扎妥当了。这是他记事以来头一次有人注意到他受伤,为他包扎,心中竟是涌起一阵感动。尔后上官若愚的所做种种,他瞧在眼里,有时分明知她不怀好意,却也不在意。因为她会留心到他是否吃过饭,是否疲惫,纵有凶险,也不会弃他一人而去。
尤其当她跟着自己落入这暗室之中后,他便对她心生亲近之意,只觉得能呆在她身旁,看她欺负陆陵,听她嬉笑怒骂,自己心中便也跟着开怀起来。这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之事。
却听上官若愚冷笑一声,道:“那不是我为人宽厚,只是你的师门寡情薄性罢了。”
付展风笑而不答。见她态度冷淡,便也就不再说了。他是聪明人,知道她心中未必对自己便有什么深仇大恨,如今这样冷待,不过就是为了上一代的师仇罢了。自己若是真诚待之,她未必便会一如既往地恨意浓重。
过了一会儿,见她的脑袋不住低垂,又强撑着抬起,终是不忍,开口劝道:“你安心睡吧。彼时我昏睡之时,你也不曾狠下杀手。如今,展风只当是报你疗我腿伤之恩,也绝不会加害于你。付展风说到做到,若是不信,这便可赌咒发誓……”
上官若愚听他如是说,便也不再有疑,再加之实在是困倦得不行了,当下便靠在墙上,沉沉睡去。
~~~~~~~~~~~~~~~~~~~~~~~~~~~~~~~~~~~~~~~~~~~~~~~~~~~~~~~~~~~~~~~~~~~~~~~~~~~~~~~
醒来的时候,头有些沉,四周一片寂静。上官若愚动了动,发现身上盖着付展风的外套,扭头望去,只见付展风与陆陵均躺在一旁,呼息深沉。陆陵倒也罢了,付展风却不似是这般不设防的人。
她伸手推了他一把,他却身子死沉,显是受了迷药,这才昏睡不醒。正思量间,忽觉头顶骤然大亮,刺得她睁不开眼来。
头顶有人说道:“我只饶你一人性命,速速离去,若敢再来,下次便要你有来无回。”声音清脆悦耳,正是那白衣女子。
上官若愚以手遮眼,抬头向上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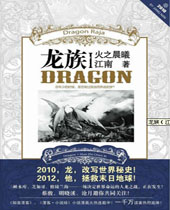
![[hp]分辨双胞胎的唯一方法封面](http://www.8kbook.com/cover/25/2573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