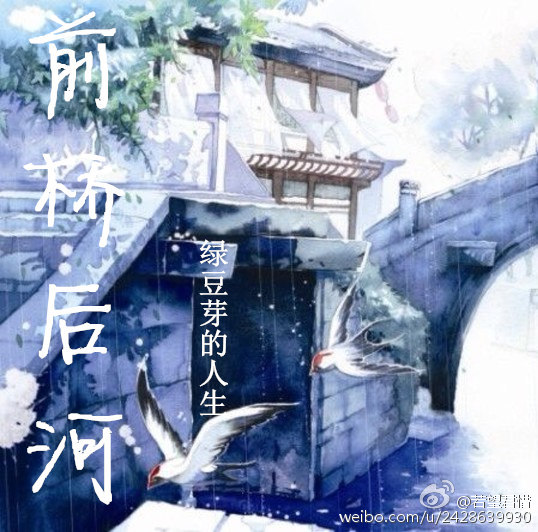伦敦桥-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可谁他妈知道他还能干什么呢?他来这儿肯定是有理由的。”
马霍尼安排好特工看守所有的电梯,然后,我们开始系统地从底层向上逐层搜查。纽约市警察局派来的后援也已经上路了。很快就会出现几十名警察。甚至是上百名。“野狼”在大楼里。
马霍尼和我从楼梯继续向上追。
“这是去哪儿?还有多远?”
“房顶。那是唯一的出口。”
“你真的觉得他还有逃跑计划?怎么会呢,亚历克斯?”
我摇摇头;我怎么知道?他在流血,一定很虚弱;也许已经神志不清了。要不就是他确实还有个计划。该死,他总是预先做好各种计划。
于是,我们一路追上去。楼顶在九层,但当我们把头探出楼梯间时,却没有看到“野狼”。我们迅速向各单位询问情况;没人看见他——如果看见了,他们是不会这么快就忘了的。
“在后面。楼顶上还有楼梯,”一家律师事务所里的人告诉我们。
奈德·马霍尼和我又爬了一截楼梯,然后站到了阳光下的天台上。还是没有看到“野狼”。只有一个一层的小建筑,就像老建筑上的那种帽子式的小房子。水塔?管理员的门房?
我们推了推门;门上了锁。
“他肯定就在周围。除非他跳下去,”奈德说。
然后,我们看到他从塔楼背后绕出来。“我没跳下去,马霍尼先生。我好像告诉过你不要插手这个案子。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快放下你的枪。”
我走向前。“是我带他来的。”
“当然是你。你就是不知疲倦、永不放弃、冷酷无情的克罗斯博士。所以你容易被人猜透,还有一点用处。”
突然,一名纽约警察从我们出来的那个暗门钻了出来。他看到了“野狼”,然后开了枪。
他击中了“野狼”的前胸,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他一定是穿着防弹背心。这个俄罗斯人像狗熊一样咆哮着,冲向那个警察,不停地挥舞着胳臂。
他抓住那个惊恐万分的警察,把他举起来。我和奈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接着,他把警察扔下了楼顶。
“野狼”朝另一边跑去,他看上去就像真的已经疯了。他在干什么?突然,我想我知道了。南侧邻楼与这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这样他就可以跳过去。这时,我看到一架直升机从西边飞了过来。接他的?这就是逃跑计划?千万别再发生这种事了。
我在他后面紧追不舍。马霍尼也是。“站住!快站住!”
他在我们前面疯狂地以Z字形跑着。我们开枪了,但第一轮射击并没有打中他。
然后,“野狼”跳了起来,双手在空中挥舞着——他就要跳到对面的楼顶上去了。
“你个混蛋,不!”奈德大叫着。“不!”
我停了脚步,仔细地瞄准,然后连开四枪。
《伦敦桥》第119章
“野狼”不停地摆着双腿,看起来像是跑在空气中,但他已开始下落了。他的胳臂伸向了对面楼顶的房檐。他的手指够着了房顶。
马霍尼和我跑到所在的楼顶边缘。“野狼”跑得了吗?不管怎么说,他总是有办法。除了这次——我知道我打中了他的喉咙。他会被自己的血呛死的。
“下来,混蛋!”奈德冲着他大叫。
“他快不行了,”我说。
他确实不行了。那个俄罗斯人掉了下来,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挣扎,一声也没吭,也没有叫喊。一声也没有。
马霍尼向下朝他大喊着。“嘿,‘野狼’!嘿,狼人!下地狱吧!”
他掉下去的动作就像是电影中的慢动作,但他还是重重地跌到了两栋楼房之间的过道上。摔得很重。我向下看着“野狼”摔在地上的身体和包满绷带的脑袋;这是我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满足。真的很满足。我们抓住了他,他也就配这种死法,像人行道上的虫子一样被碾死。
奈德·马霍尼像个疯子一样鼓掌、叫喊、跳舞。我不像他那样,但我理解他现在的感觉。下面的那个混蛋就应该落得这种下场。冰冷地死在小巷子里。
“他没叫,”我最后说,“连喊都没冲我们喊一声。”
马霍尼耸了耸宽厚的肩膀。“我才不管他喊没喊呢。我们在上面,而他却躺在下面的垃圾堆里。也许这就是公正。哦,也许不是,”奈德说着,笑着,走过来紧紧地拥抱着我。
“我们赢了,”我告诉他,“他妈的,我们终于赢了,奈德。”
《伦敦桥》第120章
我们赢了!
第二天早上,我跟奈德·马霍尼以及他的助手乘“贝尔”直升机飞回了匡恩提科。他们在人质解救队的总部庆祝“野狼”的死去,但我却只想回家。我要告诉奶奶今天别让孩子们上学了,因为我们要一起庆祝一下。
我们赢了!
在从匡恩提科去华盛顿的路上,我就开始给自己减压了。当我到家时,当我向往着家庭庆祝会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加接近正常人,几乎回到了本来的我,至少是我所认识的自己。没人出来到门廊里来接我,也许是奶奶和孩子们都没看见我回来。我决定给他们一个惊喜。
我们赢了!
前门没锁,于是,我走了进去。屋里的灯开着,但我却没看到人。也许他们想给我一个惊喜?
我悄悄地走到后面的厨房里。灯开着——盘子和银器已经被摆在了餐桌上——但是屋里还是没有人。
真奇怪。有点不对劲儿。小猫罗丝“喵喵”叫着钻了出来,靠在我脚边蹭痒。
最后,我大喊了一声:“我回来了。爸爸回家了。人都哪儿去了?爸爸打胜仗回来了。”
我冲上楼,可楼上也没有人。我找了找,看他们有没有给我留什么字条。什么也没有。
我跑下楼,走到外面,在屋前的第5大街上来回走了一趟。街上连个鬼影都没有。奶奶和孩子们在哪儿?他们知道我要回来了。
我又回到屋里,给奶奶和孩子们可能去的地方打了几个电话。其实,如果奶奶带孩子们出去,她一般都会留下字条,哪怕就出去一个小时,更何况他们知道我会回来。
突然,我觉得很难受。我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就给胡佛大厦的几个人打了电话。我最先联系的是局长办公室的托尼?伍兹。与此同时,我又看了看屋子周围,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一队技术人员来了,没过多久,其中一人走近站在厨房里的我。“院子里有些脚印,可能是男性的。房子里也有最近才带进来的土。可能是维修工或是送货的,但绝对是最近才带进来的。”
这就是那天下午他们的全部发现,没有别的线索,什么都没有。
到了晚上,桑普森和比利也过来了,我们坐在一起等着,等着电话,等着有事发生,等着希望的到来。但没有电话,凌晨两点后,桑普森回了家。比利一直等到十点左右才走。
我整夜没睡——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人跟我联系。没有奶奶和孩子们的任何消息。我用手机给贾米拉打了电话,虽然这能让我好受点儿,但还不够。那夜没有什么能帮得了我。
清晨时分,我站在门口,满眼血丝,来回打量着街上。我突然想到,这一直是我最深的恐惧,也许是所有人最深的恐惧,那就是,独自一人,形孤影单,而你最爱的人都身处可怕的危险之中。
我们输了。
《伦敦桥》第121章
电子邮件是第五天到的。我简直没法看下去。当我往下看的时候,真有想吐的感觉。
亚历克斯,我看到。
给你一个惊喜,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残酷无情。真正残酷的人,真正不讲道理的,我们都应该害怕的人,他们大部分都在你们美国和西欧。我现在得到的钱会帮我阻止他们,阻止他们的贪欲。你相信吗?你应该相信。为什么不呢?他妈的为什么不呢?
我要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为汉娜、达尼艾拉和约瑟夫所做的一切。我们欠你的,我会还你这个人情,“你是个臭虫,但至少你还是个臭虫。”你的家人今天就能回家,不过现在我们扯平了。你再也见不到我了。我也不想见你。如果我想,那你就死定了。我保证。
克拉拉?切诺霍斯卡,
野狼。
《伦敦桥》第122章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也不会就这么算了。“野狼”闯进了我的家,带走了我的家人,虽然他们毫发无伤地回到了家。但这种事还会发生的。
在随后的几周里,我加强了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之间新的合作关系。我让隆?伯恩斯对当前的局势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往中情局的兰利总部跑了十几趟,和从高级分析专家到新上任的局长詹姆斯?窦得的每个人都谈过。我想知道关于托马斯?韦尔和那个他帮助逃出前苏联的克格勃特工的资料。我需要知道他们之间的一切。这可能吗?我怀疑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这并不能阻止我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我被召到了伯恩斯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发现伯恩斯和中情局的新局长正在里面的小会议室里等着我。看来有戏看了。要么是件好事——要么就是件非常、非常坏的事。
“进来吧,亚历克斯,”伯恩斯说,像往常一样热情。“我们谈谈。”
我走进去,坐在两位重要人物的对面;他们都穿着衬衫,看起来就好像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工作日。谈什么?“野狼”?还是一些我不想听的事?
“窦得局长想跟你说几件事,”伯恩斯说。
“是的,亚历克斯,”窦得说。他原本是纽约一名律师,然后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中情局的局长。他最早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然后又在利润丰厚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干了几年。有传言说,窦得在当律师时干的有些事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
“我刚到兰利上班不久,”他说,“说实话,这种锻炼确实挺有帮助。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调查韦尔局长的一切资料。”
窦得看着伯恩斯。“资料上的所有内容都是优秀,那真是一份完美的服役记录。但这种挖掘旧记录的事可不会受到弗吉尼亚那帮子‘老英雄’们的欣赏。坦率地说,我才懒得理会他们会怎么想。
“一个名叫安顿?克里斯特亚科夫的前苏联人曾被中情局招募,并在1990年被带出了前苏联。这个人就是‘野狼’。这一点,我们可以非常肯定。他被送到了英国,在那里他见过几名特工,其中就有马丁?洛奇。然后,他又被转移到了华盛顿郊区的一栋房子。他的身份只有几个人知道。但现在这些人多数都已经死了,包括韦尔。
“最后,他被转移到了他自己选择的城市——巴黎;在那里,他见到了自己的家人:父亲、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12岁。
“亚历克斯,他们住在离卢浮宫两个街区远的地方;住在一条几星期前刚刚被炸毁的街上。他所有的家人都在1994年时被杀了,除了克里斯特亚科夫自己。我们相信那起袭击是由俄罗斯政府组织的,但是我们没法确认。但肯定是有人把他的藏身之处泄露给了那些不想让他继续活下去的人。那次袭击可能就发生在塞纳河上那座被摧毁的桥上。”
“他认为那是中情局和韦尔干的,”伯恩斯说,“他还责怪我们的政府参与了那次行动。也许从那以后他就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