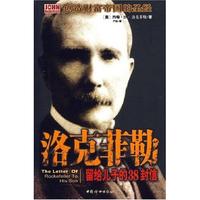怯懦者的儿子和1999-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的眼泪为什么这么贱呢?我对于善于流泪的女人要无情——谁知道眼泪是血的同胞还是水的同僚。
“玉夫,你真的很恨我吗?”
“恨?我为什么要恨你?你是我的仇人吗?”
“玉夫……”
“徐瑶!”我不想听她说话:“我不会恨你的,我想我会祝福你的。”
“你是在讽刺我吗?”徐瑶有点悲情。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别开了头。我是想真心祝福她的,可是心理怪怪的。我别开了头,匆匆走进家门,点亮了一只蜡烛(注:1999年,为了供沿海城市人夏日用电高峰,内地农家电是常被拉闸的,有人说,这就是西电东送。——李俊良,2006年第三次修稿。)——我不想让女人看见我流泪。
“玉夫,我知道你很生我的气,其实……”
她跟了进来,放下手中的小提包,欲言又止。微微停顿了一下之后,她接着说:“我来的时候想了很多安慰你的话,劝你回去的话。可我一看到你,心里的内疚又使我不知道该如何说。”
徐瑶啊徐瑶,你如果不说话,那我也就如看你的照片一样了,为你的美丽和我的伤感,我无需掩饰我的喜与悲。
她走到我身旁,递给我一个皮夹:“给你,我希望下星期能在学校看到你。”
见我不接皮夹,她哭了。
原来她哭的时候是那么的美丽动人:抿紧的唇逃避眼泪的咸;斜昂的头抑制泪的冲动;起伏的胸脯缓和内心的伤感……
月光透过窗子,投射在她身上,把蜡烛光衬显得更加灰朦朦的。
在银色的夜光下,她是那么的娇弱,是那么的纯洁。
右:在银色的夜光下,她是那么的娇弱,是那么的纯洁。
左:不,不!我嫉妒的男人已经不只一次拥有了她,玷污了我眼中乃至我心灵深处的纯洁。
右:现在,她要给你皮夹!一种象征财富的皮夹,能解决你现在的拮据。
左:她的肉体,属于了另一个男人,难道她的灵魂还会眷顾着我?
右:也许,有那么一点吧!所以她不辞劳苦,来找你了!
左:她来找我,就是为了表示一下她的慷慨!
右:一个皮夹,里边是钱,是一笔可令你暂时摆脱困境的钱。由一个女子,一个与你有过恋情的女子给你。
左:这怎么可能,难道我值得她真爱我一无所知?否则便是她又无聊了,想到了我,于是便用那种纸张的财富来消遣我,她不是总说我是一个“楞呆子”吗?再说,这世上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在男人中我已很不幸了,如果再接受女人的怜悯和施舍,我会更加的不幸,又还有什么生存的价值。
右:你真爱她吗?难道你多天以来对她的思念不是真的?
左:不,我怎么可能还会爱她!
右:你真的不爱她吗?那你为什么不敢看她。
在银色的月光下,她是那么的娇弱,婀娜。
“她的肉体,属于了另一个男人,难道她的灵魂还会眷顾着我。”
我的思想开始混乱,我的心跳开始加剧,就像一个沦为乞丐的人,即将沦为一个贼时一样。
我贪婪地看向她,看向在银色的夜光下,娇弱、“纯洁”、婀娜的她。
右:有人说,人有两种性格,一是“兽性”,一是“理性”。托尔斯泰就做了很深的研究……
左: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喜欢批评名人,好像只要能批评几个有头脸的,他自己也便有头脸了。
我能感觉到我眼中的邪恶,脑中一个声音在说:“她和你恋爱,和别的男人上床。”这声音在不断反复,不断增大音量。
我再也不管什么“兽性”战胜“理性”,也不论什么“理性”战胜“兽性”,只知道我心里“纯洁”的姑娘我没有拥有过一次,而别的男人已经拥有了多次。
我忘记了她是别的男人的女人,只觉到我的贪婪与内心的不平衡,狠狠地把她递给我的皮夹摔到一边。
她本来还在回忆着说她来时想好的话,突然她停下了,惊住了。她被我突然的举止惊住了,开始倒着步子慌乱地退却。她看出了我的欲望和我的邪恶。
她像一个亲眼目睹过车祸的女孩面对迎面而来的卡车而又无从逃避一样,苍白了脸色,瑟缩了身子。
“不——玉夫!”她摇着头,发着抖,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我无情的双手抓住了她挥动的双手,把她推靠着墙。
“我要你为欺骗一个不幸的人付出代价。”我成了一个变态狂。我的手撕开她的衣裙,嘴里却可耻地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借口,就像一只饥饿的狼想要吞食一只喝水的小羊。
“玉夫,不要!不要对我这样!”她哭出声来。
我的手伸进了撕开的裙口,触摸到了她的肉体……
突然,她不再说话,不再哀求,不再抵抗,眼睛直怔怔地盯着我,眼中充满了仇恨,其中找不到一丝以前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柔情,只有仇恨,只剩下仇恨。“
“她的眼中为什么这样充满仇恨,不眨一下。”我不再吻她的脸,我犹豫了。
她斜视着我,她的眼泪无法模糊她的这种我第一次看到的眼神。
她的眼睛大大地睁着,眼眶中的泪一圈圈地汇拢,然后顺着已有的泪痕缓缓划过。她恨出了泪,恨出了血,恨出了灵魂,眼睛不眨一下。
她恨的又恰恰是一个“曾经”深爱她的人。
我被镇住了,松开按住她双肩的手。
“对不起!”我低声说了一句,急步走开,走到柴门边。
为什么?我狠狠地一揪头发,瘫坐在石阶上。
大花挣脱了铁链,跑到我面前,伸着舌头哈着气,摇晃着脑袋,摆弄着尾巴,还不是地把爪子伸到我胸前。
我轻拍大花那毛茸茸的头。
左:那一刹那,我被徐瑶的眼光镇住了。就在那一刹那,我就像是被无数薄而利的刀在身上拉了无数道口子,感到是那么的可怖,使我惧怕一切——包括我自己。
右:你也是人,你的思想中也有自私。
左:可那是我吗?
我流出了泪。
右:你必须承认自己。
我推开大花狗,它乐得我推开它,跑了出去。它是很少有自由的机会的。
我又狠狠地揪着头发,可无法抑制住心的恐慌——我的手抓住她的手时,心就比产生了欲望时的心跳得激烈。我还第一次触及了她软软的胸脯。
她会恨我一辈子的。我这时才明白以前对她做出的傲慢是多么可笑。我对和我初恋的她的恋情是难以忘却,不能不在乎的。哪怕她的肉体已属于别的男人,只要她心里还有我,我会为她做一切。可是现在,我又野蛮地想要占有她,她不会再爱我了——我将永远得不到她的关怀——她正是出于对我的关怀才来找我的,可我却野蛮地想要占有她。
她恨我了,虽然我只是撕开她的衣裙。
她恨我了,她已看清我邪恶的嘴脸。
我为以后有一个女人恨我而无地自容。
月亮已升到半空,多么的明亮,可惜只有半张——为什么可恶的星星已抢去了她的一半,那丑陋的黑云还要扮成一只狗的模样,想要吞噬她剩下的那一半纯洁呢?
哦,天啊,刚才我是做了什么?
外面传来了大花狗惨痛的叫声和一个孩子的哭声,继而是春嫂的骂声。
大花夹着尾巴跑了回来,在我怀里哼唷着。春嫂的喊声随着她的脚步来了,大花鼓起勇气狂吠着要冲出去,我忙使劲抓住它脖子上的皮带,重新用铁链将它拴好。
徐瑶站到了门边,身上穿着我的外衣。我低下头,无颜看她。
春嫂探着脚步走来:“玉夫,狗拴好没有?”听我说“拴好了”,她才放心走进院子,手中提着一根木棍。大花叫得更急,我喝住了它。
“以前伦叔在的时候,你家大花不是拴得很好吗?现在放了,一出去就咬人。小朝阳和他们‘躲猫猫’,又没招它惹它,它就在小朝阳脚肚子上咬了一口。”
“对不起,春嫂。你先带孩子去打针,过两天我给你钱。”
“现在叫我去那里找钱给他打针?”春嫂说。这时大花又“汪汪”直叫,春嫂手中木棍一指,说:“你再恶,看哪天不把你打狗肉吃了。”
这时,徐瑶慢慢地走过来,含笑对春嫂说:“大姐,这是一个意外,玉夫也不想的。孩子咬伤了,可不能大意。”说到这儿,她从皮夹里掏出150元塞到春嫂手中,说:“明天带孩子去打针。”春嫂一边推辞一边说:“要不了这么多!”徐瑶硬塞给她,说给孩子买点营养品。春嫂这才道谢接过,叮嘱我一名“记住把狗拴好,别再放了”,看了看徐瑶一眼,撇了撇嘴,回头走了,自言自语的不知说些什么(注:听人说现在被狗咬伤不打疫苗了,得改打血清,按体重算价,每斤2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被狗咬了,至少得花2000块钱,所以很少有人养狗了,很多狗的也打杀了。这要是在西方国家,可能就不只是“人权”问题了,至少“狗权”问题得提上议案——李俊良,2006年第三次修稿。)
“有些凉,穿上吧!”徐瑶脱下披在她身上的我的外衣,然后递给我,胸前被我撕坏的裙角拴成一个小结,白色的乳罩的一角还是露了出来。
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柔和:“徐瑶,我……”
“你还没有喂你的大花吧?我帮你喂。”她朝我笑了笑,说:“我刚来的时候,它叫得很凶,后来我给了它一些饼干,它开始不吃,仍是叫。后来它用鼻子闻了闻,可能也饿了,便一边吃,一边低叫几声。”她说完笑出了声,脆脆的,刚才在她眼中的仇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找不到任何痕迹,就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也像我得知她和孙宛立(她男人)的事后她自然地同我招呼一样。
我弄不明白她的宽宏大量,我无法使自己面对她的笑,那会使我更加惭愧,让我难以原谅自己。
大花并没有咬她。她将她来时在车上吃剩的蛋糕、饼干倒在喂狗的铝钵里,大着胆子伸手抚摸大花的背脊。
“徐瑶,刚才我……”
她打断了我,傍着大花冲我笑:“你看,它不把我当陌生人了。”说罢,又是抚摸大花,又是叫大花和她握手。
“恐怕你也还没有吃饭吧!教我做,怎么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把抓住她的手。她用手掩住我的口,不让我说话,然后将头靠在我肩上,让我的手环抱着她的腰……
月亮的半张脸是那么的明亮,使人能看见石榴红色的花顶花瓣。石榴叶子的绿虽然不明显,但在月光下,却油油的亮。
月亮停在半空,空中的云却在不断变化。
水墨作就的云带,一层透着一层,连绵缠绕,微微波动。天边的白云无可奈何地卷进了灰褐色的阴云口中,只露出淡淡的红褚的光,似一把梳在云髻上的苗家女子头上的木梳。
接着,云层布满了半边天空,只用各自不同的色调来表现自己的羞怯或是自己的愧疚。然后,微微的,又是无声息地、渐渐使由于月光才有的淡淡的彤色浸透自己的身躯。
不知何时,从天边涌出一大群黑色的骑兵,撵着一层光亮的浪潮,将柔弱的彤云淹出鲜血后扩散在自己的浪潮之中。那些稍微强壮一点的彤云,也被浪潮锋利的牙一块块分割,成为浪过处一个个小岛。浪潮被迫分流,天空成了一幅帖在天空的巨画——山、小溪、树木、村庄……
最后,彤云不再是彤云,他们已被黑色的骑兵征服、渗透,最终也穿上了黑色的盔甲,逐渐聚拢,将浪潮纳入行囊……
浪枯竭了,天空是一片黑色的营帐。
不远处传来了钢琴声,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是莲婶,现在的张家园只有莲婶会弹钢琴,张家园也只有莲婶有钢琴。
不断反复的音符使人流连。
“玉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