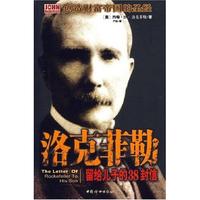怯懦者的儿子和1999-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心很空,很怕,也很苦。”
快结婚的女人,心是不是都很空,很怕,也很苦。如果黄慧愿意嫁给我了,那时,我要问问她,问问她的心空吗?怕吧?苦吗?不行,这样问她她会生气的,她会说:“一个女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找到了真爱。她的心是充实的,感到安全的,也是甜蜜的。你这么问我,肯定你不是真爱我。”然后,便会伤心地哭 ,不再理我。
天空中没有朋亮,是一片灿烂的星空。
天空中也没有云层,是一片灿烂的星空。
星星用不同的光亮,把天空铺成了不同的层次,使苍穹缀满了迷人的珠宝。
两年前,我读大二的时候,在一个星夜里,我被群星的璀璨吸引了,吹了一夜的风。结果,我发烧昏迷了,住进了学校附进的正德医院,徐瑶整整守了我三天。为了照顾我,她瘦弱了许多。
出院后,又是一个星夜,我们一起去看星空。那一天,我们看、见了流星。我没有找“现在几点了”这一类的理由,握住了徐瑶的手,指着划过的流星,默默地念:
爱神的箭穿过您的心脏吗?
不见血,不见泪
只见您纯洁的心灵
擦亮了锋利的箭端
更加明亮,更加显眼
用它
可以去寻找另一颗纯洁的心灵
徐瑶流泪了,她问我纯洁是什么。
我开玩笑说:“纯洁就是在恋人生病时和他形影不离。”
她用伤感的声音问我:“你说我纯洁吗?”
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已经是孙宛立的女人,我只知道我眼前的她是一个真诚对我的姑娘。我大着胆子搂住她的腰,轻轻的在她的额头吻了一下,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她的身体有些发颤,她用手捧起了我的脸,给了我长长的吻。那便是我的初吻,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靠近异性,我的心剧烈地跳,我的脸烫着了徐瑶的手。
徐瑶关切地问我:“玉夫,你又发烧了,你还没有好?”
我握住她的手,说:“不,不是的。”
她脉脉含情地望着我,悠悠地说:“玉夫,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我这儿得到吻的男人。”
她撒谎了,她骗了我。在那片小树林,她不是任凭孙宛立搂着,和他一起,当着我的面,“哧哧”的亲嘴吗?
不复存在的梦
只会将我对你的思念
化作一道
遥远的虹
夜,成了多情的少女,在衣裙上缀满群星,含笑笑就一弯眉月,只为你去读她。
今夜的星空,升起了一弯眉月。
今夜的星空,飘来了一身灰裙。
我拿过我的小提琴,拉起了《怯懦者的儿子》:
月亮不见了,星星仍在天空。
外边有人叫了起来,人们也喧哗起来。
我停了下来,跑出门外。
听人说,恒伯妈逃了出来,放火烧了房子……
回城
恒伯妈死了,我又耽搁了几天。
无论什么变故,道德还是不道德,正义还是不正义,总会有人沦为牺牲品,只不过后世对他们的称谓不一样。
我迟迟不能回城,太德叔有些恼怒了。姑父早已火冒三丈,说我故意不回城,是不愿提携杨清。
他们是不知道我对黄慧的思念的。
如果姑父知道以后我又要做老师,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黄慧也打电话来寄给我一些理解型的抱怨。
大刚仍努力想说服我和他开公司,并给我很长的时间考虑,说:“一个月时间,我先代理经理,一个月内只要你来,经理便是你的。”我只是奇怪他对自己母亲的过逝看得很开。
我居然会被他们如此地看重,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没有毕业,辍学在家的师范大学的学生。
我犹豫了。
左:我是一个男人,就这么为了黄慧,甘愿平凡?
右:平凡的岗位也能有不平凡的创举。
左:那是对傻子说的。
右:这种傻子活得充实,有价值,受人尊重。
左:这不是价值,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你可不要在我面前谈什么奉献。
右:爱本身就是奉献。你能说你没有爱吗?没有爱是可怜的,。那么多可爱的孩子,难道你不爱吗?
左:社会并不可爱!
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可爱的人就能组成可爱的社会。
左:那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右:不!你太过于关闭自己了,你应该能看得更宽阔的。
左:你说我是“井底之蛙”?
右:这是你自己说的。我的意思是要你敞开心扉,多去感受这一个社会。
左:我的眼前是一片迷雾,我的心里也是一片迷雾。而我没有一匹能为我在迷雾中识途的老马。
右:你有!
左:在哪儿?是什么?
右:是你自己和你的思想。
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右:你会明白的。——想想“心连心”艺术团!
左:我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
右:你会看到的。
左:他们在哪儿?
右:在奉献中!(注:有朋友对我说,该团有的团员为了争火车包房闹得面红耳赤,只不过想组团旅游,是谈不上什么奉献的。但我觉得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是不能以点概面,一概而论的。——李俊良,2006第三次修稿)
……
恒伯妈死了,怎么死的并不吸引人,让人关注的是,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恒伯妈在换着死的方法。而他们的“师父”,在外面撑起伞后,一面重竖自己的旗帜,一面对诸如恒伯妈之类的死法予以了否定。或许值得他肯定的应该是网络电视和WEB吧。
太德叔同意我带杨清一道去,并无为难之说。我们准备走的时候,大刚开车来到我们身旁,说他也要回去,叫我们搭他的车。
车到省城后,杨清不愿再和我去太德叔的工地,而是加入了大刚的“清洁公司”。
我对他说:“你是该好好清洁一下了,别总让姑妈担心。”
他不耐烦地说:“你管得也未免太宽了吧。去找你媳妇吧,说不定她早就痒得受不了了呢。”
我攥起拳头要打人,大刚忙拦住,说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有别的意思。然后又对我说:“一个月的时间,我等你的信儿。”
我没有说话,瞪了杨清一眼,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要给我爱的爱我的姑娘一个惊喜。
(第三部完)
第四部
恒伯妈死了,我又耽搁了几天。
无论什么变故,道德还是不道德,正义还是不正义,总会有人沦为牺牲品,只不过后世对他们的称谓不一样。
我迟迟不能回城,太德叔有些恼怒了。姑父早已火冒三丈,说我故意不回城,是不愿提携杨清。
他们是不知道我对黄慧的思念的。
如果姑父知道以后我又要做老师,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黄慧也打电话来寄给我一些理解型的抱怨。
大刚仍努力想说服我和他开公司,并给我很长的时间考虑,说:“一个月时间,我先代理经理,一个月内只要你来,经理便是你的。”我只是奇怪他对自己母亲的过逝看得很开。
我居然会被他们如此地看重,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没有毕业,辍学在家的师范大学的学生。
我犹豫了。
左:我是一个男人,就这么为了黄慧,甘愿平凡?
右:平凡的岗位也能有不平凡的创举。
左:那是对傻子说的。
右:这种傻子活得充实,有价值,受人尊重。
左:这不是价值,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你可不要在我面前谈什么奉献。
右:爱本身就是奉献。你能说你没有爱吗?没有爱是可怜的,。那么多可爱的孩子,难道你不爱吗?
左:社会并不可爱!
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可爱的人就能组成可爱的社会。
左:那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右:不!你太过于关闭自己了,你应该能看得更宽阔的。
左:你说我是“井底之蛙”?
右:这是你自己说的。我的意思是要你敞开心扉,多去感受这一个社会。
左:我的眼前是一片迷雾,我的心里也是一片迷雾。而我没有一匹能为我在迷雾中识途的老马。
右:你有!
左:在哪儿?是什么?
右:是你自己和你的思想。
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右:你会明白的。——想想“心连心”艺术团!
左:我没有看过他们的演出。
右:你会看到的。
左:他们在哪儿?
右:在奉献中!(注:有朋友对我说,该团有的团员为了争火车包房闹得面红耳赤,只不过想组团旅游,是谈不上什么奉献的。但我觉得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是不能以点概面,一概而论的。——李俊良,2006第三次修稿)
……
恒伯妈死了,怎么死的并不吸引人,让人关注的是,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恒伯妈在换着死的方法。而他们的“师父”,在外面撑起伞后,一面重竖自己的旗帜,一面对诸如恒伯妈之类的死法予以了否定。或许值得他肯定的应该是网络电视和WEB吧。
太德叔同意我带杨清一道去,并无为难之说。我们准备走的时候,大刚开车来到我们身旁,说他也要回去,叫我们搭他的车。
车到省城后,杨清不愿再和我去太德叔的工地,而是加入了大刚的“清洁公司”。
我对他说:“你是该好好清洁一下了,别总让姑妈担心。”
他不耐烦地说:“你管得也未免太宽了吧。去找你媳妇吧,说不定她早就痒得受不了了呢。”
我攥起拳头要打人,大刚忙拦住,说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有别的意思。然后又对我说:“一个月的时间,我等你的信儿。”
我没有说话,瞪了杨清一眼,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要给我爱的爱我的姑娘一个惊喜。
(第三部完)
选择
黄慧穿上白大褂,更显得窈窕可爱了。可我有点儿讨厌那顶白色的圆帽子,因为它把黄慧的头发给遮住了。相较之下,我还是喜欢护士头上戴的那种扁形的帽子。
黄慧见了我,很是高兴,但门诊部里禁止喧哗。她把我送给她的花往办公桌上一放,把我拉到园子里,埋怨说:“怎么不先打电话给我说一下。”我没有说话,从衣兜里掏出了准备的礼物,递给她。
她笑吟吟地接过,问:“这是什么?”
我说:“一个穷小子送的便宜的但又贵重的礼物。”
她娇嗔道:“废话!”好奇地打开包装盒。
那是我为她买的一对蝴蝶形的发卡(这就是我讨厌那顶圆帽子的原因),还有一个重音回琴。
“多漂亮的发卡!——口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吹口琴的?我可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呀。”
她拿起口琴,试了试音,吹起了《约定》……
一分静谧,一分宁静,也是一分炽爱,一分热情……
园子里散步的病人们开始注视她,她害羞了,没有演奏下去的勇气——刚才是一时兴起,没有过多地想到其他人的存在,见人们围过来,她本来就是一个腼腆的姑娘,便停了下来,脸蛋通红,像京剧里花旦的脸。
“小医生,怎么不吹了?”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在老伴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身旁,不无遗憾地说。
他的老伴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说:“什么小医生大医生的,医生就是医生。”
“她本来就是一个小姑娘,不叫小医生,难道叫大医生,老医生?”老人不服气,开着玩笑说。
黄慧被逗笑了,不由得抬起头,羡慕地看着两位老人,又转头看看我。
老人冲我笑着说:“小伙子,有点像我。当年,我就是听见我老伴吹那首曲子——《莫斯科郊外的晚上》——la do mi do re ——do xi mi—— re—— la——不行了,气不足了。那时,我就留意上她了。后来,买了一个口琴给她,她呀——就答应我了,一直到现在。”
“看他说得自己多了不起。这么容易,收你一个口琴,就答应你了。当年,可是你苦苦地追了我三年我才答应你的。”老伴又拍了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