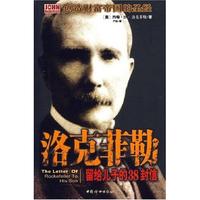怯懦者的儿子和1999-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天,收工后,大家在工地附近的一棵大皂角树下歇息,黄伯开着玩笑说:“我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要是能收玉夫做干儿子就好了。”
我还没开口,老孙伯接过话道:“有人恐怕收干儿子是假,为黄慧找朋友是真。”
黄伯说:“我本来就是想收干儿子,与黄慧可不相干。”
老孙伯说:“那就说不准了。不过老弟,你可别糊涂,可要先问问玉夫有没有女朋友。”
我不由得想起了徐瑶,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会想我吗?
黄伯有些生气了,说:“你呀,老封建!现在的年青人,哪个还要父母做主的?”
这时小波把晒得黝黑的脸凑到他面前,说:“黄伯,那你连我也收了吧。我是一个知足的人,见面礼你打发一两百块就够了。我马上给你磕头。”
黄伯用手推开他的脑袋,连说几声“去”,不想用力过大了,小波跌了个四脚朝天,他顺势爬转身来,还真给黄伯磕了一个头,说:“黄伯,看来你不想收我做干儿子,那就收我做女婿吧。”老孙伯从旁边一把揪住他的耳朵,骂道:“你瞎搅和什么。”黄伯冲老孙伯瞪眼,说:“你也不见得少搅和了。算了,算了,我怕你们,我不收干儿子了。”老孙伯松开揪小波的手,冲大伙笑道:“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打自招了。老黄是害怕收了玉夫做干儿子,以后‘干儿子变女婿’的话不好说出口,所以变卦说‘不收了’。”弄得黄伯哭笑不得,只得说了句“开个玩笑,瞧你那德性”,竟自回工棚睡觉去了。大家哄笑了一阵后,又拿我和黄伯的小女儿黄慧扯在一起取乐(确切地说,是拿我和“黄慧”这个名字在一起取乐,;因为我从未见过黄慧。)弄得我狼狈不堪——也许,这就是太德叔所说的得寸进尺吧,我倒是很喜欢这种得寸进尺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
成顺安对我的太度并没有改变,而是变得更冷漠,在大家拿我和黄慧在一起开玩笑过后,这种冷漠又变成一种仇视,使我感到畏惧,也使我莫明其妙。
“也要改变他对我的看法!”我又对自己说。
可是用什么办法改变呢?不可能再把他当榜样。如果继续拿他当榜样,我也会对我自己冷漠和仇视的。
管工记(续)
“以前每个星期黄慧都要来工地的,这几个星期怎么不来了。”
小波对我说:“她长得可漂亮了,人心肠也好,我要是能娶她做媳妇这一辈子可就知足了。可是我是不可能娶好的。”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知道我配不上她。人家是医学院的大学生,面我只是一个挑灰浆的小工人。”
“怎么这么没有信心,说不定她会喜欢你的。”我说:“要不要我帮你对她说。”
我有些想见黄慧的渴望了:大家把她说得这么好,她究竟长什么样儿?
“别!就算她会喜欢我,我也是不可能娶她的。”
我有些奇怪他前后矛盾的话,问:“为什么?”
“她年纪比我大,文化比我高。”
“这有什么不妥吗?”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小波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见我摇头,便解释说:“娶媳妇要娶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最好小那么个四、五、六岁。因为女人一结婚,生了孩子就特别容易老,而男人对性……”他顿了顿,脸有些红,见我听得很认真,便接着说:“男人对性生活的要求时间要比女人长,如果娶一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妇人做老婆,以后性生活不协调,最终也是要闹离婚的,到时候苦的可是娃娃。”
“那她文化比你高,是因为你害怕得‘气管炎’了!”我笑着说。
“原来你是知道的。”小波有些生气,说:“欺骗年纪比自己小的人是最不道德的行为。”
我笑了:“这是谁的名言?”
“当然是我的名言。”小波顿了顿,看看四处没人,便凑近我说:“玉夫,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不要对别人讲。”
我说:“你既然害怕我给别人讲,干脆就别告诉我了。”
小波又向四处看了看,低声对我说:“成哥喜欢黄慧。”
我心里不禁一酸。
心想:“我该不会因为一个我从没有见过面的女人吃成顺安的醋吧。”可解释不了心里为什么会发了一下酸。也许是大伙常拿我跟“黄慧”这个名字扯在一起开玩笑,在我的意识中晚无意识地把“黄慧”这个名字看成了我的女友的缘故吧。可又想不明白,刚才小波说想娶她的时候,我的心里却异常的平静,一点儿酸的感觉也没有。难道无意识中,认为小波与我,豪无竞争优势可言,成顺安则不同,他人缘极好,而且年纪较大,显得成熟稳重。
“不会吧,怎么从未听人提起过?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忍不住追问。
小波“嘘”的一声叫我小声点儿,然后才低声对我说:“我也是昨晚上才知道的。”
昨晚上?难道昨晚上黄慧来工地和成顺安幽会。
我心里更是酸楚难当。
看来,我真的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在吃成顺安的醋了。平时大家拿我和她的名字扯在一起开玩笑,总是说“黄慧这样这样好”、“黄慧那样那样好”、“黄慧怎么怎么好”……原本我心里还在牵挂着徐瑶的,后来做梦,居然梦见“黄慧”了,只不过她的面貌是模糊的,隐隐约约像徐瑶,又像魏伶燕(怎么也会想到魏伶燕,我也说不清楚。)
“昨晚上我闹肚子起夜,看见成哥搂着……”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他们还亲热了。
嫉妒的火焰“腾”地一下子燃了起来,心里却是一阵冰凉。又是火又是冰的感觉,怪怪的,不是那么好受。
“搂着裹成一团的被子在……”小波做了一个我看不懂的手势,接着说:“嘴里还‘黄慧’、‘黄慧’地喊呢!我想不到成哥平时看上去正儿八经儿的,原来也会用那种方式暗恋人。”
“黄慧”二字虽然只是两股气流,但我听辨得非常明白,是“黄慧”二字无疑。
原来成顺安搂的是被子,不是黄慧。我松了一口气,心里的酸味却丝毫未减。原来我还想改变成顺安对我的态度的,现在还想吗?谁知道?
今天又是星期六了,我同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做活。工程进展比较顺利,一个月下来,五层楼的主体已基本完成,剩下的是内部粉刷、铺板以及门窗的安装和外部的装饰。我们隔壁川艺公司的科技馆工程主体也差不多完工了,而长兴公司的电影院工程开工较晚,规模也相对较大,主体工程方才过半。我们三家工地虽然紧邻,但工人之间从不打招呼,最多取笑一回对方的施工技术差,夸夸自己技艺精湛,这一个月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我曾想,“其实不一定非得对抗嘛,现在双赢的例子可多了。”但觉得自己思考得还不成熟,所以没有对太德叔提及。只是有过好几回,我想和“邻居们”接触接触,试着沟通一下感情,但都没有机会。大家都在抢工期,累了又想早点休息。再则就是人还未走到他们跟前,他们先白了你一眼,然后便走开了,黄伯他们自然也反对我去跟他们套近乎,说别让人给看低了。
不管怎么说,早上太德叔来的时候大大地夸奖了我一番。
我对他说主要是成顺安的功劳,因为我对施工是一窍不通的。我又对他说了成顺安的许多优点,希望能够引起太德叔对他的重视。
太德叔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我,笑了笑,用右手按住我的肩膀说:“你见过打仗时的总指挥去冲锋吗?玉夫,记住老叔的一句话:越是靠近下层的指挥,越是远离上层的指挥。这就像现在当官的一样:越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越不能升级做大官。因为上级很多人不喜欢这样;老百姓也害怕,害怕他调走后来一个历害的,能留就尽力留,都是一个心思。你还年轻,有很多事你以后会明白的。”
我能感到太德叔这些话的荒谬,可我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反驳他,只是觉得成顺安应该被提拔,可我又不想让他为了能提拔而改变对工人的态度,所以没敢再多说什么。我只是有一点怀疑我的智力。徐瑶说她和孙宛立结婚不想让我知道,但她永远爱我的原因我以后会明白,现在太德叔又说我想要明白很多事情得等到以后,有必要这么神秘吗?我不得不怀疑我的智力了。
太德叔走后,天下起了雨。
原本计划是外墙刮糙的,也难得老天体谅,便休息休息吧。工人们回到工棚稍稍调理了一下便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有的下棋,有的“斗地主”,也有像大刚他们那样“发金花”的。
今天是星期六,我和往常 不一样的地方,仅仅是在渴望着黄慧的到来。
一上午过去了,她没有来,看来这个周末她又不会来了。老孙伯埋怨我说:“全是你小子害的!你没到工地之前,她每个星期都来给我按摩,自从你来之后,她就不来了。这两天我的腿又酸又胀的,你先来给我捶捶。”我只得放下手中的书,过去给他老人家捶腿,结果他不是嫌轻了,就是嫌重了,又把我撵开。叫黄伯道:“老黄,是不是你告诉黄慧说要给她相对象,她不好意思来了。”黄伯笑而不答,自个儿装旱烟抽。我心理则想:周末是年轻男女约会的好时间,也许黄慧和她男朋友约会去了,心里又不免有些空空的感觉。又想起徐瑶,每到周末,她都是要回家的,又不肯带我去见她父母。我总是舍不得她走,她总是先亲我一下,然后说:“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不都是在一起吗。距离产生美啊!我星期天就回来!只是星期六不见,你不会变成一个女人了吧!那我就要变成男的,天天把你搂在怀里,好不好?”记得当时我突然脱口说了一句话:“这是不是小别胜新婚。”马上又觉得不合适,顿时脸燥热难当。她脸色似乎一变,见我不自然,又转而笑了,低着头轻轻问我:“你想要新婚的感觉了?”我更加尴尬,想起在寝室里郭明他们说与女朋友偷欢的事,于是壮着胆子看向她的眼睛,却发现她的眼中有一股忧郁之色……现在我是明白了,她是爱我的,可是她也不能离开孙宛立,每个周末她都是去和他相会。
老孙伯见黄伯不答理他,哼了一声,便拉过被子盖住双腿,倒在床上,不一会儿便打起了呼噜。黄伯则在一边抽旱烟一边自言自语:“大概在忙考试吧,她说过要争取拿第一名领奖学金的。但愿她能考好,我这身子骨可撑不了几年了。”他咳嗽了几声。成顺安关切地问:“黄叔,你不要紧吧。”我也忙递了一件衣服给他披上。
“没事,只是抽得急了,呛住了。”
“那就少抽点吧。”成顺安去给黄伯夺烟杆,没有夺过,只得由他。他自己适才闷得慌,是一连抽了好几支烟的,可是仍然闷,坐不住,便起身拿过安全帽戴上,没有给我好脸色,莫明其妙地瞪了我一眼后,走了出去。小波放下手中的吉它,问他去干什么,他头也不回,只随口答了声“上厕所”。
我则拿出李俊良送给我的英文版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y),心不在焉地默背那著名的开头: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