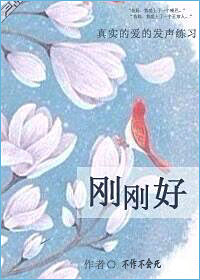不会游泳的鱼-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董勇只能看见她的背影,看着她的手腕子一升一降的,待她转过脸走出来时,他看见这些动作对这张脸的重塑,那是一个要上台的浓妆重彩的潘凤霞。潘凤霞在台上浓妆艳抹,在台下却极少化妆,素面朝天,她是占着天生丽质。如果她化妆就是带着演戏的意味,生活中也处处是戏。比如今天。他想,看来有一台戏等着她去演。
丁丁过来对发愣的董勇说:“卫生间里没有厕纸了。”
“你妈妈不是从餐馆里带了一包餐巾纸了吗?”
“我是说厕纸了。不会听中国话吗?”
“英语就罢了,中国话也轮得上你教我吗?笑话。”
丁丁立刻就翻起她的白眼球,意思是:这日子她过够了。
两个孩子对父母婚变态度相反。董海比以前更安静,什么也不说。董丁从来不反对妈妈出去约会,她从来只问一个问题:“他有钱吗?”潘凤霞想,这哪像她女儿啊?倒像她势利眼的妈。丁丁是这样想的:与其要她将来为钱牺牲爱情,还不如让她妈妈为她去为钱牺牲爱情。这样她连爱情也不用牺牲了,这样她就可以提早过上有钱人家的日子。她坚信:作有钱人的女儿比作有钱人的妻子日子好过。
电话是帕特打来的,问潘凤霞有空吗?如果有空,想请她过来聊聊。潘凤霞放下电话就开始打扮,现在打扮好了,就出门了。
董勇正系鞋带准备跟出去看个究竟,这时门铃响了。董勇以为潘凤霞丢了东西,就去开门。突然一个金发碧眼的不迅之客出现在门口。一张由大大的太阳眼镜和血盆大口组合的脸,嚼着口香糖,不知道已经这样嚼了多久,腮帮子都显出疲劳来,可是只能这样嚼下去,反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丰润的舌唇轻微地招惹,有个笑停留在嘴角上。
门外的亮光白成一片,门内是暗淡的一片,金发少女的出现夹在黑白两色间,具有极强的反差、侵入性。董勇一脸的惊愕,本想客气地盘问一番她是不是找错门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英语要让她听懂,可能得把她累死,于是也就放弃,等着少女自己开口。
少女摘下太阳镜,露出青春四溢的脸,说:“你好。我找海。我是他的同学,我们约好来借他的课堂笔记。”
董勇隐约地听懂,却不确定,叫:“海海,出来帮着翻译一下。”
海从房间跑出来,短裤,赤着上身。他有半分钟的反应不上,敞着两扇嘴唇愣在那儿,突然一溜烟跑回自己房间,再出来时,身上多了件长衫、长裤,还原在学校的样子。
雯妮莎知道自己正被中国视线网住,不得动弹。董勇、海海、丁丁,父子三人在窄长的门廊形成一只中国侦察队,盯着这个白种女子。那种盯法让雯妮莎觉得他们不是在看她,而是在侦察她。对于这些中国人,她的意图与心思需要他们这些眼睁睁得研究。这种盯法让她感觉自己真有一些隐晦难懂。
//
…
第八章把裤子脱了,把衣服脱了(2)
…
门外是余下的暮夏白昼,依然炎热。她抵着门站着,世界就这样被挡在外面了。
雯妮莎立刻道:“对不起,我来晚了,路上堵车堵得厉害。”
海海发觉自己的嘴还半敞着,又听见雯妮莎说:“谢谢你让我借你的课堂笔记。”
海海立刻领会了这个接头暗号,而且很自然地接道:“噢,噢,对,没关系。”
海转过头对父亲说:“我同学,向我借课堂笔记。”然后领雯妮莎进房间。
董勇看着儿子带着一个高大的美国女孩进房间,有点摸不出头绪,莫明其妙地问丁丁:“这个白女孩是谁?她找你哥干什么?”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哥哥的同学来借课堂笔记。”
双胞胎兄妹儿时是冤家对头,经常互相告状,彼此作对。长大却相互包庇、相互结盟,倒不是明白骨肉情深的道理,只是懂得,他们其中一人出事,别一个也没好处,父母总是一起惩罚。于是彼此虽然互相贬损,但面对父母、外人,却统一战线,一致对外。
父亲也看出这一点,问也白问。可也没觉得什么,一个女孩儿还能把他儿子怎么着?想想,董勇就出门了,接着跟踪潘凤霞去。
“你怎么来了?”进了自己的房间,海海还是那样直睁睁着他,好像从她进门眼睛就没眨过。
海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孩子,也从不讳家穷,可雯妮莎这样一下子逼近了他的私人生活,他第一次感觉到来自贫穷的自卑。可在雯妮莎眼里,穷不是无可奈何的生活状态,而是一种风格与情调。就像她好端端的牛仔裤上挖好几个口子一样,是一种时尚,一种标新立异的风格。
“我在电话里不是告诉过你要给你一个惊喜吗?”雯妮莎完全感觉不到海海的不自然,好奇地东张西望。
“就是这个惊喜?”
“对啊。上次我失约,你不高兴,所以这次我来个惊喜,希望你高兴。”
海海是高兴的,她是怎么知道自己住在这里的?
“你最近为什么没来找我了?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问。
海海想了一会儿,实话实说:“没有,只是每次你找我,都是要我帮你写作业,可我不想帮你写作业。”
雯妮莎夸张地叹了口气:“和男孩子相处真难,要么他吃醋,要么他怕你榨取他的劳动力而躲你。”
他笑了,说:“那你就别榨取人家的劳动力。”
这时丁丁端了两瓶可乐进来问他们渴不渴,雯妮莎定眼看了看丁丁,笑眯眯地,嘴角向上翘翘,“呵,你妹妹长得挺漂亮的。”
丁丁却被她赞美出了受辱:自己漂不漂亮,凭什么由她来评价?自己是一件摆设吗?她大方又大声地回答雯妮莎:“你也漂亮。”
她们都不是在表达对对方的欣赏,而是把漂亮当作头衔加冕给对方。
雯妮莎说:“谢谢。”潜台词是:“谁怕谁啊。”
后来丁丁出门倒垃圾,走时故意重重地关了一下门,不知是要威胁还是要安抚自己的哥哥。
“家里就你和我了吗?”雯妮莎问。
“对。”
隔壁一家一如既往地在放色情录像,一阵阵“啊啊啊”。雯妮莎听了大笑,笑声如同爵士乐一样不当回事又放浪,海海却不敢笑,笑就是承认想到那种事了。现在家里就他们两个人,怎么能想到那种事呢?这个不自然使海海不停地天南海北胡扯,不停地吸可口可乐,吸到瓶底发出“咀咀”的干涸声。
雯妮莎突然大声地敲响墙壁:“小点声,这里还要学习呢。变态狂。”
海海吓了一跳,他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都不敢出声,雯妮莎一来就抗议上了。
隔壁却故意把音量调得更大,雯妮莎气得用鞋子拍打墙壁,大骂:“变态狂,变态狂,变态狂。”
海海想不能就这样卡在这里尴尬着,总得做点什么来分散那浪叫声。
“我们来点音乐吗?”
“好啊,你喜欢什么音乐?”
海海从小是听戏曲长大的,喜欢古典一点的东西,但是他想这样可能不够酷,像个小老头,就说:“我喜欢各种不同的音乐,除了古典音乐外。”
“我也是。”雯妮莎说完就去调了一台摇滚乐。
海海问:“你为什么喜欢这种奇怪的音乐?”
她回过头笑:“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很奇怪吗?”
然后跟着音乐起舞,她的舞步自由热情,带一点野蛮,一会儿她拉着海海一起跳。海海不会跳,也就跟着扭了扭。海海的跳舞其实就是快步走,他拘束惯了,一下子敞不开来。两个少年人在不明不白的傍晚灰色中翩翩起舞。
屋内有点热,她脱下外套,贴身的背心露出凹凸有致的身躯,鼓鼓的胸与纤腰有那么大的起伏。他见少女先撩拨头发,对他笑,笑得热络。她那么成熟与久经沙场,十七岁的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是招惹,使她优美的少女形象带着一种放浪的潜质,一切却恰恰吸引着他。
//
…
第八章把裤子脱了,把衣服脱了(3)
…
两个人离得那么近,相互的气息都进入对方的生物感知。他突然希望一个动作,一个可以作证他们的一个记号。他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希望什么动作。他艰难地咽回直流的口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没……有。”
海连忙把眼睛移开,却来不及把眼光带走。就像钓线收回来了,鱼钩却留在鱼身上。
雯妮莎盯着他的眼睛笑:“还说没有?”
“我想吻你。”海海突然被自己无辜的声音吓倒。像他这样胆子不大的男生,反而容易脱口而出一些想也不敢想的话。是荷尔蒙惹得祸,它可以使人胆大妄为到平日想像不到的地步。
而且讲英文的他似乎有了另一种性格,让他大胆、直率的多,可以冲动、冒昧;而他的中文太成熟了,太瞻前顾后了。用英语表达“我爱你”比中文容易的多,用英语直言性爱与凶杀也比中文容易的多。可一说完,说中文的海海会突然脸红起来——这些话我可说不出口。
“嗯,”雯妮莎听了,并不意外,而是笑笑问,“为什么?”
“你等一下。”海海突然转身去书架找书,找到一本,迅速地翻到一页,朗诵道:“趁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光,还我的心来!不必了,心既已离开我胸口,你就留着吧,把别的也拿走!”
海海不流利、带中国口音的英语让这段古典诗词听上去特别的古怪、搞笑,雯妮莎笑得弯腰,一直叫肚子痛。海海在一边呆呆地看她笑,像是自己乍有其事地做正经事,却被人当相声听了去。他想她可真能笑啊。
“你在读什么?”
“拜伦的《雅典的女郎》。”
“想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我临行立下了誓言,请听:我爱你呵,你是我的生命。”
“好了,别再念了,说点自己的话吧。”
“这也是自己的话啊。我喜欢你,不,我想我爱上你了。”
“你说什么?”她蹙起眉大声地问他,她是担心他的英语不灵光,用错了词汇。
“我想我爱上你了。”海也完全没料到自己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大真话。
“你想你爱上我了?”
“我知道我爱上你了。”他说每一个字时都一本正经,诚心诚意。
她沉默了两秒钟,再次大笑起来,她觉得这是她这十七年里听到最幽默的表白。一会儿后也觉得这样不好,拼命忍住,最后还是没忍住,于是也就随它去了。她快活地躺在海海的小床上开怀大笑,一阵狂笑,仰天长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以后她会发现:她不留情嘲笑的十五岁的少年给予她的真诚与爱,是她这一生最珍贵的礼物。如果她当年把它理解为爱情,如果这个世界把它当回事的话,那么她和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世故了。
“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这时她看见海海的脸色在她忽强忽弱、忽大忽小的笑声中,忽红忽白,忽笑忽哭。她才正经下来,“我们可以吻了。”
而海却早已没有情趣:“算了,我们还是跳舞吧。”
雯妮莎突然起了怜悯之心,说:“星期五晚上忙吗?说不忙。”
“为什么?”
“这个星期五,我带你去派对。”她还是那么不管他同不同意,已经替他做了主。
“什么样的派对?”他是想趁她讲述的时候考虑要不要去?如果她希望他去,她是会尽可能把酒吧讲得生动诱人。
她偏不说:“去了就知道。记住:八点。”
“谁说我要去了?”
“你会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说过你爱我。”
她那么自信,那么郑重地调戏着他。纯洁的海海又是一阵脸红,然后很认真地说:“如果你不能到的话,你就现在告诉我,我好有个心理准备。如果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