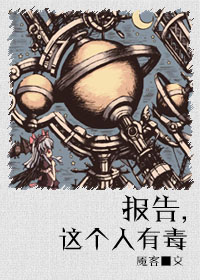青春的敌人-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发现,自己至少有一身不算时髦但却清洁的衣服。尽管走进四星宾馆会感到超豪华设施带给自己的无地自容的压力,可那里毕竟不是我们天天出没的地方。在其他场合,这身衣服并不显得寒酸。我们去公共食堂,去中档餐厅,去运动场和电影院,去赴老朋友的约会,它都很适合。我们不用在每次出发前苦思冥想地排练,觉得哪件衣服都不算合适。看到穿着5000元的西服,上了汽车连坐下都怕弄脏衣服的人,我们很可怜他们。我们一时贫寒,却有幸没有使自己沦为衣服的奴隶。
我们发现,自己有一辆老式脚踏车,从重庆骑到北京要花掉我们50多天的时间,就算在市内奔忙,也难说不会被骤然袭来的一场山雨和看不见的尘埃弄得皮肤发痒,还有赤日炎炎的焦灼。可是,我们用不着为何时给它加汽油而担心,也无须交什么养路费,车祸的可能性也不算大。那些拥有飞机的老板,有着比飞机更大的麻烦,而我们只是骑着自己的家藏破车,像堂·吉诃德骑着他的瘦马,走自己的路。我曾经三次从北京大学去房山县云水洞,所乘工具一次是汽车,一次是火车,还有一次是自行车。第一次简直虚无得很,从起点到终点,匆匆而去,匆匆而归。第二次我们必须先骑车到永定门火车站,然后乘火车,由于我自作聪明,男生被送上了去周口店的火车,我领着女生上了直抵目的地的列车,然后一路惊险。可我觉得那才是生活。现在,那些女生都已结婚生育,但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朴素的岁月,还一直不能忘记那些穿着洁白的连衣裙,在薄薄暮色中无辜受罪地跟着我走进野山坡的女孩子们,也忘不了第二天在孤山口与男生相遇时的欢腾。第三次是我自己,献了200CC血,换了90元路费,只身去十渡和山顶洞,路经云水洞。那是四月天,我骑着破车,在漫漫无期的盘山路上感到醉心的静谧,在寒水冷月中的深夜,体尝着山里的风。我在云水洞小宿了一夜,静静地想起两年前的往事。尔后又去周口店,与老祖宗和农民们厮混了几天。有时候,人们游览风景变得像是在赶赴人潮拥挤达到摩肩接踵程度的足球联赛场,而不像是去感受自然荒野的寂静和纯洁,他们打算在最少的时间里看完最多最美的东西,匆匆地拍照,匆匆地跳下旅行包车,又匆匆地跑回旅店,蒙头便睡。他们走过很多地方,却没有增长灵性。可是,脚踏车却可以使我们感受到老式生活中那种厨房伙计的充实。
我们又想到,自己有几本好书。那是我们生活发生深刻转变的几个催动点,有一些闪光的人物以及里面细腻的篇章是我们熟悉的。有时,一看到它们就想起往事童年的终结,青春期的探知、受过伤害的爱情继而,我们发现,从前的记忆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这样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是贫乏的,你怪不得它。你应该怪自己还不够像一个合格的诗人那样,唤醒它的财富。因为,对于创造者来说,世界已没有贫乏,没有贫乏而无关紧要的地方。即使你蹲在监狱里,它的墙壁使你听不见世界的喧嚣,那么你不是还有自己的童年这笔精美珍贵的财富,这座记忆的宝库吗?〃是的,即使我们不幸生长在上海里弄最破烂不堪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因为童年的贫寒而没有一个美丽的日子,如果真是那样,我们恐怕早已成了残酷的打劫者,站在强盗的行列之中。然而,我们没有那样,也没有自杀,在我们最为无聊的时候,还是站在纺纱机前,在噪音严重污染的车间里受着文明秩序的约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有过夹杂着美梦和零星快乐的时光。
我们还有五六个要好的知音。还有充裕的时间,它不能像钱一样储蓄,却可以随时在生活中提取。还有洋溢的思想,也许大亨们原来也有,后来渐渐遗忘,也许那些走红的艺员从来没有,只有一张父母遗传的好脸,我们可以在肚腹中咯咯地笑他们造作,再笑笑那些不知道叶利钦是何许人也的小业主们,他们是贫穷的财主。
我们发现,自己有许多劳动成果。尽管作出它们之后,我们再没有拥有它的机会,或者按照某个更为合理的标准领取创造它们的报酬,可那毕竟是我们的杰作。法拉第在进入皇家学院前,介绍人告诉他,科学研究要付出极大的劳动,而所得却甚少,然而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报酬。〃我的好朋友陆,本科毕业后没有马上去作厉以宁院长的硕士生,而是向研究生院打了先工作两年的申请报告。也许当年的300元月薪并不符合他在北京制呢厂销售科的操劳,他可以马上拿到学位,毕业后谋个更好的差事,或者去美国。可是他告诉我,他不打算马上离开这家工厂,因为他亲手制订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才300块工资,但你看到一个集团在自己的计划下运转,那种快乐就是补偿〃!后来,陆上完研究生,又回到制呢厂。一九九七年,陆二十九岁,却成了这家国有大厂的厂长。
这样想下去,我们简直就是个富翁。我们不过只是用暂时的陋具在栖息和云游。我们采用这种离生活更接近的方式,完全是因为我们想把事情看得更真切些,得到更原始更真实的厚重感,这正如坐在坟地的荧火中所感到大地上曾经劳动、歌唱、生育过的人们真的一去不返的历史感,远远超过我们坐在火葬场烟囱旁边得来的一样。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特点,但虚无是它致命的弱点。当我们发现我们有的,比如劳动成果带来的欢欣,大亨比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沮丧。因为我们的成果最容易被我们察觉,我们看到街市的人们穿着自己设计的花布,或者喝着自己灌装的饮料,我们的自豪就比非得抱着一叠烦人的资产损益表才能从枯燥的数字里发现成果的百万富翁,来得真切。我们的财富是直观的。
▲ 伟人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贫穷,甚至比自己还惨,所以不必自卑。另外,真正折磨我们的,往往不是伟人们也曾有过的贫穷,而是他们曾经避而远之的金钱贪欲。
M·C·Eschelr一八九八年出生在荷兰一个水利工程师的家里,中学时曾两度留级。后来,他由学习建筑,转而专攻绘画,但老师对他的评语是:〃缺少青年的心境和朝气,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人。〃不过,Eschelr锲而不舍,周游欧洲。假设他按照传统的方式,在肖像和动物画中继续努力,他很有可能在同时代的版画家中,夺得一席体面的位置。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画越发心理化,越发突出画面中的潜在冲突,越发热衷于对规律性、数学结构、连续性、无限性的描绘。他不再坚持在外部视觉中散发美感,而是在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道路上探索,因而他失去了评论界和拍卖商的兴趣,而且知音无几。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Eschelr的画才被数学家、物理学家、结晶学研究者发现,因而走红火暴,使他大发其财。但此前的漫长岁月中,Eschelr一直过着水平线以下的生活,经济上完全由父亲支持。
一七九四年一个阴沉的黑夜,二十五岁的拿破仑沿着塞纳河堤心情沮丧地走着。孩提时被贫困压迫,年轻时受政治迫害,现在他离开了军队,身无分文,几乎想带着二十五年的辛酸往事,投入一江寒水。
大作家W·福克纳因为生计问题,小学五年级辍学,去作房屋油漆匠和洗盘子的杂工。他一度梦想上大学,可是一年级就因为语言考试不及格而被迫退学。后来,他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谋到了邮政局长的职位,但因为他总是把邮件搞得乱七八糟而引起了群众的愤怒。直到二十五岁之后,福克纳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走上了后来使自己富有的写作道路。
杜鲁门总统在青年时期的穷途困境,更令人难以忍受。由于视力不佳,他没能进入美国西点军校,他在药店、银行、装瓶厂、铁路调车场等等十几个工种尽心尽职,境遇却很长时间没能更改。林肯和孙中山,还有许许多多大人物也都曾有过比我们难过多少倍的艰苦生活,甚至还倍受虐待,但他们却坚忍地承受着艰辛,用恒久的努力,打破了它们的重重围困,在排除了贫穷之外,又排除了平凡。
电影界把一九八八年称作〃王朔年〃。这一年,王朔的四部小说《顽主》、《浮出海面》(电影名《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电影名《大喘气》)被改编成电影,轰动了中国,把评论界扰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观看,权威们风声鹤唳地批判。那一年,王朔和崔健占据了青年人的大半个心灵。可是,不知有多少会知道,当王朔一九八四年退职并于次年开办了餐馆时,他过的却是极端穷困的生活。那时,他与舞蹈艺员沈旭佳相依为命,沈旭佳跳一场舞只能挣5块钱,并且不得不吃掉大部分工资奖金,以强化身体。因此,他们从经济拮据到人情的恶劣,体会到了五味俱全的生活。直到一九八六年〃一半一半〃在《啄木鸟》杂志发表,他们的窘困才得以初步缓解。回首那段时常饿肚子的日子,王朔没有嫉恨它,依旧像当时那样泰然视之。他说,人在贫穷中怨天尤人,是因为额外的欲望。在《我那令人难以理解的追求》一文中,王朔说
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很可能,我们受到的不是贫穷本身的折磨,而是变态的贪欲被阻止时的不满。伟人也一样经历过贫穷,但之所以伟人没被贫穷当场打倒,是因为他们对金钱的态度是散淡的。他们争夺世界时,往往并不把金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是为实现崇高理念而奋斗,物质财富只是随之而来的东西。这就是常人所说的,一心挣钱的人,得不到大钱,当我们有了伟大襟怀时,大钱却会自己来。很难想象,一门心思要挣点钱花,能使林肯奋斗成美国总统,或使王朔写出《看起来很美》。即使艾柯卡转道克莱斯勒公司想给福特公司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他的主导目标也不是使自己单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按照美国人的复仇方式,在同行业中依靠竞争手段,打败对手,报小福特把他从总裁贬为零件仓库副主管的一箭之仇。从健康欲望上讲,这些有钱人是愉快的。
希罗多德说:〃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这是准确无误的发现。我们并不是说,应该减少追求物质幸福的欲望,而是说,第一,这种欲望的确应该有个止境,第二,这种欲望的满足,常常可以或者必须不以挣钱为直接目的。
▲ 在《人的文学》和许多散文里,周作人写道:十六世纪发现了人,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但愿二十一世纪,我们能发现真正的生活。
柏拉图在《国家》一书中,记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阿曼托斯的这样一段对话
苏格拉底:〃当一个陶工变富了时,请想想看,他还会那样勤苦地对待他的手艺吗?〃
阿曼托斯:〃定然不会。〃
苏格拉底:〃他将日益懒惰和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