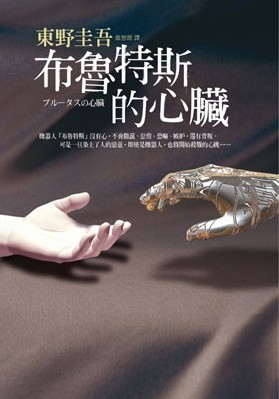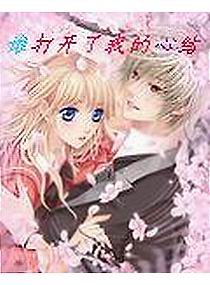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嘶ḿ馍暇∏樘荆楦幸淮未瓮平葡蚋叻澹詈螅退睦侄右黄鹜瓿闪艘淮位曰偷那楦幸鞘健V富痈行凰侄拥娜烁行凰壑诟歉行凰P以卺∧簧系囊衾种辍窨路蛩够遣皇且不岣行徽馕恢泄暮⒆幽兀�
郎朗受到的欢迎是激动人心的,就是不得第一名,光享受这种掌声、喝彩,也是不虚此行。他一遍遍返场,一次次地行着大礼,依然迈着他父亲为他精心设计的那种过于沉稳的“小大师”步子……
别忘了,我们是在日本仙台比赛。别忘了,还有一位叫作上原彩子的日本女选手。她是上届柴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第二名,第一名轮空,她耿耿于怀。她此番出征,就是要夺冠,夺取第一名!这是不含糊的。否则,她没有必要参加比赛。她是日本的希望,也是夺冠呼声最高的选手。从那些一开始就围着她转的那些记者,那些火箭炮筒似的摄相机和照相机,都在对准了她。而没有任何记者会注意到中国的郎朗。这倒也好,让郎朗有了安宁,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集中精力练好曲目。
上原彩子占尽“主场”之利,她是雅马哈公司出钱培养她,送到美国深造,还为她请了一位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指导。她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好像她是当然的无可争议的冠军。一般我们通常认为日本孩子弹琴注重精确,而往往在音乐上弱,可是,上原彩子在技术和音乐上同样出色,在精神上更不肯示弱。她的确很有实力,演奏时显的沉实坚定,充满自信的力量。她当然会大受欢迎。
还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普列马托夫,他长得人高马大,弹钢琴时有种居高临下之优势。他比郎朗大两岁,却要高出差不多一个脑袋。郎朗是纯粹的小孩,可他却是个真正的大人。从他来自的国度看就有优势,老柴属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以他的名义命名的音乐会怎么能够不看重来自他们国度和民族的选手?如果从有利角度而言,他们都比郎朗更有着夺冠的优势。冠军究竟会落在谁手?
最忠实的听众郎国任,在听完六位参加决赛选手的演奏后,他深感震惊。特别是日本的和俄罗斯的选手发挥极佳。他们都有可能折桂。但是,他更看好自己的儿子。郎朗比他们更能打动听众,郎朗弹得更有光彩,因此,郎朗所受到的欢迎是空前的。他一次次谢幕,一共谢了四次,还是难以抚平场上的热烈潮水。观众们涌到了后台,把后台门堵得严严实实,为得是找郎朗签名。看到儿子在这片欢呼的潮水中起伏,郎国任更是心潮难平。
比赛结果,郎朗如愿以尝,获得第一名,而那位上一届的第二名日本的上原彩子这次又得了个第二名;又一次遗憾。获得第三名的是俄罗斯选手普列马托夫。
9 月10日这天,获奖选手表演。已经获得第一名的郎朗震动了日本舆论界,他们将原先对准上原彩子的一片镜头齐刷刷调转过来,对准了郎朗。镜头面前的郎朗多少有点不适,他有点腼腆地应答着记者们的采访。记者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欢吃肉,吃蔬菜、水果;问他业余时间喜欢干什么,他说喜欢体育,爱看足球。
记者采访第二名上原彩子。记者问她你有什么感受?她答道:我又参加了一次比赛。这句话说得多有意味。
郎朗在日本名声大躁,人们热情相邀郎朗来日本演出。俄罗斯的资深评委谢尔巴克马上与郎朗签了合同,订于明年邀请他到莫斯科、日本、朝鲜、以色列、意大利等国家巡回演出。日本“NHK ”公司录制了郎朗与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的肖邦协奏曲CD光盘。“JVC ”唱片公司还录制了郎朗钢琴演奏专辑。一家演出公司还问郎朗是否原留在日本。郎朗回答得非常明确,他说他不会留在日本。但,他答应了这家公司的邀请,来日本演出。后来,郎朗母亲周秀兰也随同儿子一起来到日本。这是她第一次出国,第一次随儿子到国外演出,第一次享受到儿子给她带来的荣誉。每每说到这里,这位饱受风霜的母亲就会洋溢出一种近乎天真的动人状。令我感动。所有国际钢琴比赛没有一个家长到场,只有郎国任特殊,所以外国人见了他便问:你是老师?他如实答到:我是家长!外国人不会知道这位家长对于郎朗的重要性,便面露诧异:家长来干什么呢?
获奖选手表演音乐会的场面是相当激动人心的。选手们的精彩发挥,使本次大赛在辉煌中有了一个璀灿的句号,而郎朗的名字从此融入了仙台的广濑川河,汨汨流向日本岛。作为本次大赛的组委会主任中村广子在镜头上出现时,显得特别高雅,她的气质与周广仁先生有些相象,年龄看上去也差不多的样子。她说,她是第一次作这种大赛的组委会主任,她也是第一次遇到中国郎朗这么好的选手。她特别称赞了郎朗。她说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曲子好,但要表现出来是非常难的,而郎朗弹得出人意料的好,整个音乐都被他融入身体中,音乐理解得这么深,技术这么好,他水平确实很高,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得第一。
中村广子还颇有感触地说:通过郎朗弹琴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水平,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钢琴与西方的距离在缩小,东西方文化也在缩小。
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获得圆满成功,而郎朗父子也大获成功。郎朗不仅与同来的中国最好选手相比得到了成功,而且与世界同年龄组的高手相比也技高一筹。
赵屏国老师更是激动万分。尽管这次公布获奖名单时,他没有像上一次在德国埃特林根时那么激动,但他确实在郎朗弹完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时流泪了。他被自己的学生感动得热泪横流。郎朗在接下来所受到的欢迎越甚,他的泪就流得越欢。他在内心深处感叹着:这么小的孩子,比第二名上原彩子小二岁,比第三名俄罗斯的普利马托夫小三岁,这么小的孩子却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发挥得这么好。多了不起的孩子呀!回国后,记者采访赵老师时,赵老师说,我兴奋得三天没睡着觉。这是我经历的比赛中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意义远远超过几场音乐会……我们真正挺起了胸脯,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在谈到郎朗何以能够夺冠时,赵老师说:
郎朗其实有三个不利因素:1 、年龄较小;2 、在国内从未合过乐队;3 、决赛的曲子难度较大。对此,我抓住以下几个要点不放:
一、这次是“老柴”比赛,我再三叮嘱郎朗一定要把老柴的作品弹好;二是古典作品,除把握住曲子特点风格外,还要发挥郎朗自己的特点。比赛成功了,证明这几点抓对了。在第二轮比赛中,郎朗弹了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弹得也很出色。俄罗斯一个音乐学院的校长说:“这孩子不简单,虽然我第一次听中国曲子,但我能听懂它。”
赵屏国老师认为这次比赛许多选手失败在老柴的作品上。技巧都不错,但在风格上音乐上弹得不够好。一位外国听众说,我一听到郎朗的演奏就意识到,这个孩子肯定是懂老柴的人教的。“还问我”赵老师说“郎朗是跟谁学的。殊不知,我几乎是研究了一辈子老柴的作品。”
赵老师还告诉记者,有位俄罗斯选手的家长对他说:“我听郎朗弹琴一直在流泪,从他的弹奏中我感受到了阳光。”
作为中国唯一的评委周广仁先生说:
“在这次比赛中,中国选手更为突出。受到极大的欢迎,国外的评委评论说,中国代表团总体实力最强最好。对我们有三点评价:1 、中国的孩子有才华;2 、中国钢琴教学好,是成功的,训练整齐,技术基础打得好,较全面;3 、中国孩子弹得温暖,有表情。
他们没想到我们是这样的水平。最后他们承认——中国了不起。
我作为中国的评委,感到特别的高兴和自豪。
周先生在谈到郎朗的演奏时说:郎朗的演奏感觉好,跟观众交流亲切,很投入。作为演员这点很重要。他的抒情性能打动人。第三轮比赛时,他忽然冒出一些光采、火花来,把大家高兴坏了。另外,他和乐队合作得很好,虽然出来第一次合,但很快就很和谐了。乐队指挥说:“这孩子真了不起!”这也是一种能力。他得第一,是当之无愧的。
听到这么多美好的评价,郎国任心里边所有的委曲都可以得到慰藉了。
比赛结束的兴奋余震并未结束,郎朗他们从仙台同机回到北京。载誉而归,校长陈南岗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他们。她把一束鲜花献给郎朗,她的笑容比鲜花还灿烂。她与一行人一一握手,握到郎国任时,她说,谢谢你。
郎国任呢?一下子语塞,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一节 与殷承宗的缘份
众所周知殷承宗是中国最著名的钢琴家。他的知名度之高不仅来自他曾经荣获的柴柯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二名,而且,还因为他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中的特殊经历。他弹奏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曾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更喜欢他弹奏的《黄河》,那是一条大气磅薄的“黄河”,那种力度与厚实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尤其喜欢结尾部分那种超迈与豪放的《东方红》旋律,每次听到那里,都令我激动不已。他弹出了中华民族的精髓。
殷承宗的黄河有两个结尾,一个是东方红的结尾,一个是别的。这两个结尾分别打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烙印。对于这两个结尾,听众各有各的喜好。但是,我更喜欢“东方红”。殷承宗自己也更喜欢东方红,他到台湾演出,台湾听众也更喜欢东方红,他们为东方红这种“最强音”激动得近乎颠狂。
这些年来,殷承宗走出国门,经香港到美国,最后在美国落脚谋生,可以说历尽沧桑。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多了一种回归渴望,也许是在外漂泊的时间久了,更勾起某种故园情思,总之,他对国内钢琴的发展特别关注。尤其是对于有才华的琴童更是看重。由于钢琴狂热的持续,中国涌现出一批天份极高的琴童,他们在国内外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已经越来越为世人瞩目。
在中国这么多琴童中,郎朗是最抢眼的。他在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两个最高奖项,这很为香港钢琴界看重。殷承宗到香港时,听到钢琴界有关人士谈到了郎朗这个孩子,那份盛赞的口气一下子就让殷承宗产生了兴趣。他非常想见见这个天份极高的孩子,他不仅是爱才心切,他更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天份高的学生。几年来,他一直想在国内物色一个学生,他所要物色的学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生,他要找到最好的。
殷承宗揣着一个美好的愿望风尘仆仆来到了北京。
在中国的玄学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一位传教传功的大师会有这种神秘的经历:即儿时的某天,突然被一位素不相识的道士或高僧认领为弟子,遂撇开庸碌的世俗,从而踏上仙途。这是某种天意还是天缘?反正是越玄越好。
写书人不一定非要把殷承宗找郎朗一事往玄里写,但,这确实是件与众不同的事情。因为中国的钢琴老师奇缺,高水平的钢琴老师更是罕见,要想投入到他们门下,即便交纳昂贵的学费,恐怕也难以承诺,而如殷承宗者更是求之无门,安有送上门来找学生之理?
事实上,殷承宗正是抱着找到郎朗亲见一面的愿望,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也许殷承宗先生的了不起处正在这里。这点,让我想到了李斯特。
�